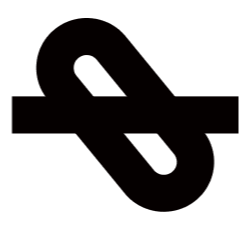封存 1994:重演、调用、残留
摘要:这篇评论从媒介理论、媒介考古、和现象学的角度,讨论王子耕的作品《1994 年》何以将他近乎私密的个人记忆从一个人流转到另一个人身上,并通过记忆与情感建立离散的共情。评论通过三个板块——重演、调用和残留——探究成像技术和空间安排与记忆之间的关系。《1994 年》通过对个人档案、文化档案与社会档案的调用,体现了当代媒介技术对记忆的外部化。与很多媒介学者所认为的不同,记忆的外部化的结局不一定是技术对记忆的控制,也有可能将散落在技术环境与建筑环境中的无主记忆收集,并把它们变成联系个人的纽带。这个过程的关键是记忆以及技术图像的碎片以何种方式被拼凑和重组。《1994 年》通过建筑空间与当代数字成像技术重新组织并连结过时的媒介,让我们重新思考重组意味着什么。《1994 年》不仅是王子耕父与子的经历在世界上留下的残影,它的运行也改变着每个人的记忆,这些改变是《1994 年》本身的残影。 关键词:媒介考古;记忆;技术;时间

《1994 年》是一个巨大的黑匣,上面布满肋条和令人不明就里的机械零件。一个惊叹号被三角形框住,让人想到或许这个容器里面装着极易碎的物品,它刚从别处泊来,已在路上漂流多久,辗转几处,不得而知。黑匣顶部有开口,里面隐隐透出昏黄的光。不管有没有人在,黑匣两端的风琴式推拉门都会不停往复,好像一个陷阱在等待着自己的猎物。(图 1 - 图 2)


图1 - 图 2《1994 年》在坪山美术馆
风琴关闭的时间是一分钟,你坐下时,灯会自动亮起,好像有幽灵在等。你会透过玻璃看到自己的脸和身体出现在玻璃的另一侧,那是舞台。你的镜像坐在床上,和你一样。你会在你的手边发现一个转轮,或许你会不由自主地转动它,在某个瞬间,你会看到一个人影跟你背对背坐在同一张床上。你不知道他或她是谁,也不知道他或她从哪来。你也许也不知道这转轮到底控制着什么,但是如果你不停转动,幽灵就会再次出现。这时候镜中的世界已经烟雾缭绕。或许你会猜到,这个幽灵其实是对侧的观者。但是你无法和它交流,或许你也不想,因为你更希望它是你认识的人。时间到了,风琴罩打开,是时候离开了,因为下一个人还要进来。(图 3 - 图 4)
图 3 - 图 4 烟雾缭绕的镜中世界
黑匣里封存的是王子耕的 1994 年,它被打包装箱寄送到你面前。这是一个调用回忆的机器,通过循环往复的运动,让观者不断在记忆和现实间穿梭。循环不仅是回忆的结构,也是人们存在于时间中的方式。根据王子耕的介绍,这个作品中展现的是他与父亲之间唯一的一段亲密时光。1994 年他父母离异,小学的王子耕跟着父亲住在这个工作室和住宅的混合体中,他的父亲租下北大燕东园的小院,作为制作树脂工艺品的工作室。货架后的床是王子耕临时的家,坐在床上观察父亲办公室的记忆成为了这个作品的起点。在《1994 年》里,"两个联动的单人剧场交互开合,通过窗口,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虚像置身在《1994 年》父与子不同的梦境里,也可以在某一个刹那与对面的陌生人不期而遇,彼此的像出现在同一个空间,却无法交流。或许你也和我一样,期待一个熟悉而又不可能出现的背影"。虽然这个作品其实是王子耕个人关于父亲的回忆,但是他认为作品同时反映了一切"亲缘关系中的依赖、对立、和解和遗憾的轮回"。 从王子耕对自己意图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记忆在个人与个人之间流转。王子耕认为,《1994 年》可以让他近乎私密的个人记忆变成群体记忆。这篇评论要讨论的问题正是记忆何以能够通过《1994 年》从一个人流转到另一个人身上,为什么一位观者可以去认领一个陌生人的童年回忆?普遍的共情从何而来?评论将通过三个板块——重演、调用和残留——从媒介理论和媒介考古的角度讨论成像技术和空间安排与记忆之间的关系。《1994 年》通过对个人档案、文化档案与社会档案的调用,体现了当代媒介技术对记忆的外部化。与很多媒介学者所认为的不同,记忆的外部化的结局不一定是技术对记忆的控制,也有可能是将散落在技术环境与建筑环境中的无主记忆收集,并把它们变成联系个人的纽带。这个过程的关键是记忆以及技术图像的碎片以何种方式被拼凑和重组。《1994 年》通过建筑空间与当代数字成像技术连接过时媒介的手法,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重组意味着什么。

“阳光做的不对,” 我说。起初他们都没回话,然后安妮问:“你说做的不对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说, “阳光在地板上移动的太快了。窗的影子从出现到地板上到从地板上消失,我每次都会计时。从一开始做这些重演实验的时候,我就开始计了,今天又计了一次,毫无疑问,现在阳光比之前走的更快了。” ——汤姆.麦卡锡(Tom McCarthy),《记忆残留》(Remainder)[1] 通过对父亲工作室空间的重组,王子耕试图在装置的黑匣之中重新建造儿时记忆中的空间。他特意营造了一种石膏质地的陈旧感。其中作为父亲空间背景的风机最为明显。虽然还在转动,这些风机却大大小小,歪七扭八,好像已经因为运转太久而渐渐变型,即将在时间中融化。消融,似乎是一切记忆的最终宿命。就像英国作家汤姆.麦卡锡(Tom McCarthy)透过《记忆残余》的叙述者所传达的那样,记忆既变化多端又无比狡猾,它会把完整的经验变成片段,并将不同的经验剪切、重组,来填补心里的深坑。如此看来,黑匣好像是封存 1994 的容器。但黑匣的封存也抵御不了熵增。这段记忆本身会在回忆的过程中变质,不仅陈旧而且不可依靠。(图 5 - 图 6)

图 5 - 图 6 王子耕父亲的工作室模型
小说中的叙述者在某次意外中被天上掉下来的某样东西砸成了重伤。伤势损伤了大脑,使得他不仅忘记了那次意外的过程,也忘记了身体该如何流畅地运动。他因此获得了大量的保险金。但由于遗忘,他被困在了自己残存的记忆中。他开始用自己的保险金搭建记忆中的场景,雇佣演员和管理者,让它们一次又一次地为他重演记忆中的片段,让他不断重新经历自己仅存的记忆。他渐渐地开始重演身边的意外,直到重演本身变成现实。最后重演变成了命案。他和他雇用的经理纳兹(Naz)劫持飞机逃亡。飞机升空以后,他再次开始了重演实验,用枪逼迫着机长在天空中不断前进回转,他想一直这样,直到宇宙毁灭。但是他知道燃油会先耗尽,而循环到不能再循环就是他的结局,因为他相信自己遗忘的记忆还在某处,等待着被唤醒。没有记忆也就没有未来。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记忆就像是神秘记事本(the mystic writing-pad),刻画下的痕迹永远不会消失 [2]。《1994 年》则可以被当做是通往这些神秘刻痕的路径。就像《记忆残余》中的叙述者一样,王子耕希望把自己重新放回到记忆中的那个场景,或许熟悉的床和货架能够让他想起什么已经遗忘的东西。这是王子耕对自己个人经历的考古与调用。熟悉的场景变成了寻回记忆的媒介,它们所能唤醒的不是被诸如电影或录音机记录的信息,而是刻在潜意识里,好像消失,却又从未消失的记忆。重演是抵达记事本中神秘刻痕的方法。(图 7 - 图 8)

图 7 - 图 8 父亲与儿子的空间
《1994 年》与《记忆残余》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对重复和循环的执着。《1994 年》的空间可以被当作被外部化的个人记忆,每次进入都是对记忆的调用。以《1994 年》中的空间为载体,浸没于剧场中的观者被传送到记忆之中,从而处于出离现实(Ecstasy)的状态。在风琴不断左右运动的过程中,观者会脱离剧场回到现实,此时观者或许会逗留也或许会离开,不论怎样她或他都开始了对未来的期盼和谋划,从而进入了另一种出离的状态。《1994 年》循环往复的结构即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 (Dasein)时间化的基本结构。存在于时间之中,就意味着不断地从当下出走,在从过去到未来的永恒循环中前进 [3]。

“倒不是因为我害羞。而是,嗯,我根本就不记得那件事了。就像一片空白或一个黑洞。对那件事,我只记得残缺的图像。蓝光,扶手,其他颜色的光。但是谁说这些就是真的记忆呢?谁说我受到创伤的心智没有自己编造,或从其他地方借来这些碎片,并用他们随意填充被撞击出的深坑?人的心智就是那么诡计多端又那么狡猾。记忆是真正的投机者。” —— 麦卡锡, 《记忆残留》 《1994 年》是一个来自不同时代的图像生产和播放装置的混合体:其中包括来自 19 世纪中叶的幽灵幻灯(phantasmagoria),19 世纪末的黑色玛丽(black maria),以及当代的数字摄影机与投影仪。黑色玛丽是摄影装置,而幽灵幻灯是投影装置,数字成像技术成为连接这两个死去媒介的纽带,并赋予了它们新的生命。(图 9 - 图 10)

图 9 - 图10 帕珀尔的幽灵(1876)及原理图(1881)

图 11 《1994 年》轴测原理图
数字摄像机和投影屏幕在空间中的安排,使得在《1994 年》中摄影和投影可以同步完成,也正因如此黑色玛丽和幽灵幻灯才得以相互渗透,共同存在于黑匣之中。藏在地下的联动装置让风琴式推拉罩无休止的往复运动,就像幽灵在演奏异世音乐。无论是儿子的空间还是父亲的空间都装有传感器,当观者坐下后,装置里的灯会自动亮起——观者的进入是整个记忆机器运转的必要条件。 媒介研究学者埃尔基·胡塔莫(Erkki Huhtamo)称像《1994 年》这样唤醒已经过时的媒介的艺术作品为以媒介考古作为方法的媒介艺术。对于胡塔莫来说过时的媒介就像虫洞,它们并不会让人摒弃现实回到过去,而会照亮新兴数字成像媒介中陈旧的部分,从而使得本来隐形的媒介从环境中显现出来 [4]。倒错时空的过程中,媒介考古艺术质疑了以技术发展为主导的目的论历史观。而在《1994 年》中,媒介考古艺术不仅是对线性历史观的扰动,也挑战了组成当代媒介环境的档案和路径。

图 12 两个隐藏屏幕和实验过程中幽灵幻象的照片
《1994 年》对媒介环境的扰动来源于肉体接触与数字图像之间的矛盾。数字图像的研究者往往认为,与模拟媒介(Analog Media)相比,数字媒介(Digital Media)与现实之间缺乏联系,因为前者是通过物理接触而成像的,例如早期的银版照相技术,而后者则将现实打碎成数字,并在电子屏幕上进行重组。在重组的过程中,模拟媒介固有的指向性就有可能丧失。包括威廉·J·米切尔(W. J. T. Mitchell)和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在内的媒介理论家普遍认为指向性与数字图像无关 [5]。维兰·傅拉瑟(Vilem Flusser)甚至认为技术图像与现实的分离早在模拟媒介时代就已经开始 [6]。世界不再由物组成,物已经被打碎成了粒子或像素。这些批判性研究的危险之处在于,学者们与深伪技术(Deep Fake)的开发者一样都在尽己所能地斩断数字图像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①。但是当数字图像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真正切断的时候,前者就会替代后者成为现实。虽然媒介理论家们的目的是让人们理解数字图像本身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客观,它们也有自己的主体性。但是这类批判的最终效果却与深伪技术如出一辙,一个全新的世界就此诞生,在那里一切真实都失去了重量。(图 12) 意识到媒介研究中批判思维的危险性,媒介理论学者克里丝·宝森(Kris Paulsen)在她新近出版的《这 / 那》(Here/There)一书中试图通过 “非物质的触碰(Immaterial Touch)“这一概念来拯救数字图像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联系 [7]。宝森认为虽然数字成像技术并没有通过物理接触而成像,但是从查尔斯·S·皮尔斯(C.S. Peirce)的符号学理论的角度来看,指向性并不依赖于物理的接触 [8]。她认为数字图像对于人情感上的触碰也是指向性的一部分,这种指向性依赖于解读者与被解读的图像存在于用一个时空中——指向性是一个事件,是解读者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非属于数字图像本身的特性。(图 13)
图 13 父子的虚象
宝森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数字图像进行的分析虽然严谨,但是她的论证方法限制了她对数字图像的物质性、成像技术以及成像过程的思考。在《1994 年》这个作品中,王子耕对机械联动装置和电子传感成像技术在空间中的安排恰恰为补充宝森论证中的缺陷提供了新的角度。《1994 年》是一个回忆机器。要调用记忆许要两个条件:机械和电子设备的正常运作以及观者在门开的时候进入黑匣的内部,成为回忆机器的一部分。当观者坐到椅子或者床上,传感器会让室内的灯光点亮,摄影机和屏幕也会在此刻开始工作。观者可以通过手摇转盘来控制对面空间顶部的灯在滑轨上的移动。在这个过程中,对面空间中坐着的人影会在被灯光照亮的瞬间,被摄影机捕捉,并实时传递到位于地上的屏幕上,从而使得虚像出现在记忆空间中可能出现的位置。为了造成一定的随机性,《1994 年》的剧场空间地上设有两个屏幕,人影会随机出现在一块屏幕上,这也意味着在玻璃隔板后面出现的幽灵正是数字图像的镜像。这个幽灵般的影子之所以能够出现,正是因为对面的空间里面也坐着一个人。两人一样,等待着黑暗的降临,挡板的升起,等待着在玻璃后面那个镜像世界里看到某个人的身影。因为两人都知道,对方的身影也会在黑暗降临的时候,在某个瞬间从记忆身处闪现。在《1994 年》这个记忆机器中,观者、阐释者、数字系统和机械装置必须同步。而正是这个经由空间和程序建立起来的同步性确保了数字图像的指向性。作为一个对细节把握到极致的装置,《1994 年》通过空间安排将重组的过程摊开在黑匣之中,成像、灯光与观者之间的共时性限制了数据的接受和传送,使得世界的碎片只能按照现实重组。如果我们承认傅拉瑟是对的,技术图像就是将世界打碎再重组,那么《1994 年》让我们看到破碎的世界并不会让指向性消失,我们需要诘问的恰恰是这个重组的过程。

“我又向窗外望去。觉得挺开心的。我们飞过了一小片云。从里面看,这片云好像是砂质的,就像在楼梯井中飘散的烟尘。最终太阳将不再升起——燃尽,砰的一声,灭绝——这宇宙也会像发条没上紧的玩具一样慢慢静止。那时就不会再有音乐,不会再有循环。又或者,在那之前,燃油会耗尽。不过现在,云歪了,失重的感觉袭来,飞机再一次倾斜并转还。” ——麦卡锡,《记忆残留》 体验《1994 年》时,人们无法控制与自己共享黑匣的人到底是谁。对于王子耕来说,随机性恰恰是这个作品的重点。他认为与人生一样,出生在怎样的家庭,成为谁的亲人都无法选择。同时,观者进入的并非自己的记忆,而是作为创作者的王子耕的成长空间。对于观者来说,陌生的环境和人组合而成的却是及其亲密的感觉。背对背同床而坐或面对面隔桌对坐是只有长期陪伴的家人或密友才可能会有的姿态。矛盾的是,这种姿态只在转动转盘的时候才会出现,陌生的陪伴也不过存在于虚妄的幻境。既然一切都是陌生的,既然 1994 中封存的记忆与观者无关,那此起彼伏的共情又从何而来呢?是什么给予了 1994 连接不同个体的能力?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继续追问,记忆在哪?如果人们能够对陌生的人在陌生空间中与自己的相对位置产生共情,这似乎意味着记忆并不仅仅存在于意识之中。像《记忆残留》的主人公一样,每个人调用无法主动调用的记忆都需要环境刺激。不仅如此,记忆和情感也存在于外部的物质环境之中,工业化的数字媒介已经成为了储存人们共同记忆的义肢。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说,义肢即截肢 [9],当技术和媒介成为记忆的一部分,也就意味着人们的记忆和情感正在向环境流失,成为了世界历史。

图 14 转盘与镜中的背影

图 15 《1994年》装置内部
法国哲学家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认为人们必须重新思考记忆与技术的关系。与书写这样的记忆技法(mnemotechniques)不同,记忆技术(mnemotechnologies)是散落在技术系统中的记忆,要调用它们,必须要遵循技术系统本身的运行逻辑。斯蒂格勒称这个过程为记忆的语法化(Grammatization)[10]。如果外部记忆储存在被科技企业控制的基础设施中,那么记忆的语法化相当于是科技企业用资本的逻辑控制着人群的记忆,不仅是外部的记忆,甚至是书写和绘画的方式,以及内部记忆与外部记忆之间的流通方式。然而与此同时,记忆的外部化也将人们以不可预料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外部化的记忆不仅属于个人,更属于整个技术环境。不仅如此,人们调用内部记忆的方式也会随着调用外部记忆的规则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记忆真如弗洛伊德所说,就像是神秘记事本,但凡刻画下的就永远不会消失,那么斯蒂格勒关于记忆与技术的讨论则说明,如何调用那些深深浅浅的刻痕,有时并不由自主。在《1994 年》里,记忆技法与记忆技术通过建筑空间的组织相互融合。虽然《1994 年》中封存的空间只存在于王子耕的个人记忆之中,但是组织这些记忆方法却遵循着外部记忆的文法,为人群所共享。黑匣中的潜在记忆既不是个人的也不是公共的,它们无处不在又无人认领,等待着人们去唤醒。(图 14 - 图 15) 只有观者进入装置,《1994 年》中的记忆调用机制才会启动。没有观者,《1994 年》就只是一个沉默的幽灵。因为人的存在,《1994 年》才存在。而它提供的恰恰是人人都会经历的普遍记忆——一段已经逝去的亲密关系,可能存在于亲人、恋人或友人之间。这些记忆并不属于谁,正像你无法选择你的家庭,你也无法选择生离死别。这些普遍的记忆之所以能变得特殊,之所以能被谁认作是自己的,正是因为《1994 年》让人们从镜中看到了自己,正是这个镜像给与了这些散落在技术网络与建筑空间中的无主记忆一个面孔。观者因为这个面孔,将无主记忆变成填补心底深坑的材料。《1994 年》引起的共情,从某种程度上,利用外部记忆的无主性,挑战了记忆外部化对时间与记忆的控制。这些人人皆可共享的记忆,变成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必要条件。经由《1994 年》的剧场效果,个体与个体相连,成为分享情感的社群。 《1994 年》所封存的就是王子耕的父亲在世上留下的遗迹,它既存在于王子耕的意识中,也存在于物质世界,这两者不可分离。《1994 年》循环往复的运动本身,是调用记忆的工作,工作的奖励是《1994 年》利用残留媒介制造的残留。观者在辨认出自己面孔的时候,将会认领如幽灵一般出没在世界各处的无主记忆。因为这些记忆是人所共有。在回忆空间与现实空间之间循环往复的运动会改变记忆的内容,而这个改变本身,就是《1994 年》的残影。

图 16 《1994 年》外观
图片来源 图 1-图 8:由 PILLS提供 图 9:Noam Elcott, Art Artificial d arkness: an obscure history of modern art and media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93. 图 10:Noam Elcott, Art Artificial darkness: an obscure history of modern ar t and media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93. 图 11-图 16:由PILLS提供 注释 ①类似的论述见 Bruno Latour,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 [J], Critical Inquiry 30, no. 2 (January 2004): 225–48. 拉图尔认为在批判的同时应该区分事实与我们所关心的事实的价值,否则的话这个世界上会变得不再有真实可言。 参考文献 [1] Tom McCarthy, Remainder [M] Paris: Metronome Press, 2005. [2] Sigmund Freud, “A Note upon the ‘Mystic Writing-Pad,’” in Organization and Pathology of Thought: Selected Source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1, 329–37. [3]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M], trans.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S.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Modern Thought, 2008, 370-380. [4] Erkki Huhtamo, “Time Traveling in the Gallery: An Archeological Approach in Media Art,” in Immersed in Technology: Art and Virtual Environments [G], ed. Mary Anne Moser, Douglas MacLeod, and Banff Centre for the Art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6), 233–68. [5] Kris Paulsen, Here/There: Telepresence, Touch, and Art at the Interface [M], Leonardo Book Ser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17, 19-25. [6] Vilém Flusser, Into the Universe of Technical Images, Electronic Mediations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7] Kris Paulsen, Here/There: Telepresence, Touch, and Art at the Interface [M], Leonardo Book Ser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17, 1-16. [8] Charles Sanders Peirce, “What is a Sign,” in Charles S. Peirce,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M], ed. Nathan Houser and Christian J. W. Kloese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9]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M], 1st MIT Press e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4, 45-53. [10] Bernard Stiegler, “Memory,” in Critical Terms for Media Studies [G], ed. W. J. T. Mitchell and Mark B. N. Hanse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64–87. 作者简介 翁佳 青年学者,耶鲁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建筑技术史与环境媒介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