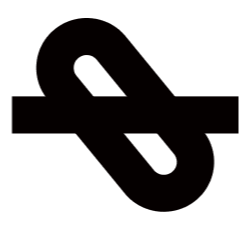激进技术 | 电插座:激进设计的幽灵

动荡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了一系列自主性设计方案(projects of autonomy),后又被总结为“激进设计(Architettura Radicale)”。尽管相隔半个世纪,我们今天去看这些激进设计时依然能轻易地产生共鸣。消费主义的狂欢,技术带来的流动性,不断延伸的信息空间……它们所描绘的世界仿佛是对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的预言。 也许是这种易得的共鸣性使得活跃在半个世纪前的激进设计在今天依然深受策展人和学院的青睐。作为一种既不受制于时间,又没什么阅读门槛的题材,激进设计变成了一种文化类时尚:你能在嬉皮士派对、展览馆或学术圈里经常发现它们的踪迹;要是想更省事一些,激进设计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美学风格。 然而,如果把激进设计放到它所在的六七十年代社会背景中进行深入解读,我们又往往会陷入抑郁。这种情绪可能来于自它和那个时代的落败——如此浩浩荡荡的运动竟然没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成果。1968年五月风暴和之后十年各种左派革命的偃旗息鼓,见证了工人阶级作为政治主体的最后挣扎,也见证了资本主义吸收并化解内部危机的强大能力。“激进设计 (Architettura Radicale)”一词是意大利艺术评论家日尔曼诺·塞兰特 (Germano Celant) 在197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的。讽刺的是,“激进设计”诞生的同时,激进设计却随着那场光荣而狂热的运动走向了终结。

“May 68: Demonstration.” (“68年的五月:游行。”)近处横幅上写有 “liberté syndicale(工会自由)” © Fondation Gilles Caron. Courtesy School Gallery/Olivier Castaing.
对于那个激情澎湃的时代,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痴迷和念念不忘,像是亲吻墓碑来纪念逝去的恋人。然而是否存在解读激进设计的其它途径呢?在急于发问的狂热和求而不得的抑郁之外,我们还能感到备受启发么?

激进设计中,科技和消费主义是经常被讨论的对象。这是一个科学技术发展到极致的世界:庞大而奇异的建筑物与低矮密集的老城格格不入,太空飞船似的巨型机器在海洋山脉间穿行。它如科幻小说般天马行空,也是对白热化的美苏太空竞赛的延展想象。 同时,这也是一个消费主义发展到极致的世界:电视机,收音机,留声机,汽车,自行车,野营帐篷……中产阶级的生活被五花八门的消费品塞满。

图1 朗·赫伦, “建筑电讯”小组,“海洋上的行走城市”,1966。 图2 Archizoom小组,“无休止城市的内部景观”,1970。
如果说激进设计所描述的科技与平庸的日常保持着令人敬畏的距离,那么消费主义已经作为一种社会常态融入了普通家庭的生活。 消费主义和技术这两个核心视觉元素,在激进设计中被赋予了两种不同表现手法:对消费主义的表达往往比较实在,它常常直接剪切消费类杂志上琳琅满目的广告素材,然后进行种类和数量上的叠加拼贴,使读者产生强烈的代入感;而对于科学技术,激进设计的视觉表达却总是奇异恢弘而浪漫。这样看来,似乎“技术”确实比“消费主义”承载了更多“激进”的分量。然而,如果尝试跳出思维定式,将“激进”的标签从“激进技术”中剔除,那么这些“神奇”的技术有没有可能和消费主义一样其实来源于某种“日常”呢?

电源插座,一个在激进设计中常见的元素,虽然通常很不起眼,但是支撑着它的电力系统却在许多激进设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理论项目《无休止城市 (No-Stop City)》中,意大利激进建筑团体Archizoom建造了由一个无限的室内空间所形成的城市。在这里,所有和栖居相关的科技发展都被推向了极致:每一寸城市环境都被基础设施技术均质化了——完全依赖机械通风,每50平方米设一个洗手间,以及全覆盖的电力系统(平面上有一个不易察觉的黑色点阵:每个小黑点代表一个电源插座,很容易和同样用点阵表达的柱子混淆在一起。) 同样来自意大利的激进建筑团体Superstudio(超级工作室) 在1972年制作的电影《超级表面(Superficie)》中描绘了人类的终极生活状态——像游牧民一样在地球这个“超级表面”上流浪,可以自由选择落脚的地方。不过有一个前提:你得先接入附近的一个“插座”,以获得源源不断的能量、食物、和信息。这个巨大的网络无差别地覆盖在所有地球表面,即使在雪山脚下一处荒蛮之地定居,也照样能享受“标准化”的舒适生活。

图1 安德烈·布朗齐,Archizoom小组,居住区公园,“无休止城市”(平面图),1969。 图2 超级工作室,“超表面——地球生活的另一种模式”,1972(视频见文末)
英国激进建筑小组Archigram在《插件城市 (Plug-in City)》和《行走城市(Walking City)》中将“插座”的概念直接升级到了整座城市的规模。这是一个由科技发展所推动的,去中心化的后消费主义社会:一座座巨构建筑,无数胶囊状的居住单元插入其中——城市本身变成了一个巨型的电源插座。除了外露的建筑结构,支撑着城市运转的其它基础设施(例如水和电力)都隐藏在结构构件的内部。“插件城市”的理念还启发了日本新陈代谢派,不过相比于前者的社会学立场,后者更偏向于表达技术本身。

彼得·库克,“插件城市:最大压力区”,1964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看似酷炫先锋的电力系统,实际上已经是一项相对成熟的民用技术了,其普及程度和当时的消费主义文化是相当的。虽然电力基础设施在六七十年代的欧洲还未得以全面应用,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普通家庭中却是再平常不过的一项居住条件了。

《美国之家》杂志,1960年10月刊内页 * 客厅正上方的大灯和桌上的台灯被视为住宅的基本配置。
照此说来,激进技术对电源插座(电力系统)的表达就应该像对消费主义那样进行现实素材的叠加和拼贴。可奇怪的是,在大多数相关的激进设计中,电源插座却依旧被当做一项陌生而浪漫的科技——小小的插座可以在城市甚至星球表面上形成一个无边无际的场域,它甚至可以抽象为一种概念,一个可以统领整座城市运行方式的想法。 对比之前提到的“技术即激进”的线索,电源插座陷入了一个灰色地带:作为一种“日常”的社会现实,插座在设计中反倒被“激进化”了。这不免令人好奇:究竟是什么促使激进小组们对“日常”的电力系统进行观点清洗(idea laundering),最终把它变成一项陌生而新奇的“激进技术”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回到电力系统的发源地:美国。

尽管美国家用电器市场在二战后如雨后春笋般爆发,但将电力作为基础设施的历史还是相对较短的。自从1752年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风筝实验发现了电,1879年托马斯·爱迪生“发明”白炽灯,以及其它几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力技术突破以来,发电和输电技术以及家用电器的发明共同经历了一段平稳渐进的时期。 最早的电器是没有电源插头这个概念的,用电设备需要直接和大量电路导线连接。美国国家电气承包商在1901年6月至1902年6月之间对马萨诸塞州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一年内有14人死于电气事故,其中大多数是由于工人不慎触碰带电电路造成的。直到1904年,哈维·哈贝尔二世(Harvey Hubbell II)才发明了第一个壁挂式电源插头。 在二战前,电力是一种稀有资源,是用于工业和大城市特权家庭的奢侈品。到1925年,一半的美国家庭用上了电,但农村地区的住户只有百分之十通电。193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百分之二十五。尽管生活在城镇地区的大多数居民都能获得电力,但由于电站成本高、传输效率低,曾有一段时间电力只在夜间提供。为了保证使用,一些大型的商用电器如吸尘器和熨斗都内置了独立发电机。而家用级别的电器往往价格十分高昂,被视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

图1 胡佛 O型吸尘器(售价60美金),1907。 图2 胡佛吸尘器广告,1931。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社会的转折点,它将美国从长达十年的大萧条中解救了出来,使它成为了一个中产阶级激增的富裕国家。1956年的高速公路法案标志着全国范围郊区化的开始。随着基础设施的蔓延,数以百万计的独立别墅从近郊逐渐蔓延到美利坚广袤而尚未开发的土地上。自然、土地和基础设施资源被重新切割并均等分配给每一所房子。州际公路上穿梭的私家车成为了宅与宅、社区与社区、旧城与郊区之间私有化的移动连接。 随着郊区住宅的扩张,美国中产阶级打开了一个庞大的电器消费市场,电力技术随之快速发展。一方面,电力不再是奢侈品,而是一项郊区房屋的基本配置,一个全国性的基础设施系统。另一方面,每一栋房屋也成为了一台功能齐全的机器:电视机、电冰箱、微波炉、吸尘器、熨斗……家用电器作为家庭主妇身体的延伸,让贤惠的她们在保持大房子干净整洁的同时,还能抽出时间看电视节目和陪伴孩子。家庭成为了高度分散的社会单元:在电器的帮助下,一所房子几乎可以承担一半的社会公共职能,远远超出了私人住宅的居住需求。私人影院、后院烧烤和家庭派对的流行让大家相信有些社交活动再也不必在城市公共空间里举行了。

图1 一家四口手牵手站成一排面向着一幢农庄风格的郊区住宅,画面左边前院里立着“房屋出售”的牌子, 1965 *1960年,美国住宅中位数售价为1.19万美金,而家庭中位数年收入就有4970美金。 图2 1950年代的美国家庭妇女
在郊区拥有一栋塞满各种家用电器的房子,就意味着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一辆私家车,和一个美满的家庭:它成为了社会身份的象征。富裕的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范例,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自然而然地,发达的电力基础设施所支撑的家庭生活就与美国的整体社会状态联系在了一起——一个更富裕、更少剥削的中产阶级社会,一个更民主、享有平等地权和消费力的国家。

同战后的美国类似,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洋彼岸的欧洲福利国家也出现了“白领”工作和服务业的显著增长。这些新兴中产阶级人士被称为“社会工作者”,而不再是资本主义早期受到严重剥削的工厂工人。于是,作为无产阶级代表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也就逐渐缓和了。 然而,欧洲和美国对这些变化的反应却不尽相同。美国迅速适应了新的资本主义,郊区化和电气机械化对居民生活的改善占据了社会主导地位。而在欧洲,左翼政党却忧心于失去工人阶级这一有力的政治主体以及中产阶级的去政治化。他们一边对所有权力和机构进行激烈批判,一边还要忙着进行学术理论的重建。尽管越来越远离政治对抗的“前线”,左翼知识分子内部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有义务揭露这似乎有所缓和的工人阶级斗争。

《红色笔记本》,1961年创刊,是当时意大利最有影响力的左翼政治刊物之一。
与此同时,左派知识分子中的建筑师们在政治挣扎之外还面临着一场空间的危机。一方面,城市中的现代主义建筑逐渐沦为服务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形式风格,意大利建筑历史学家塔夫里也称之为“退化的乌托邦”。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新模式以开放的城镇结构取代了封闭的工厂厂区,在空间中制造“产品”已经转向制造“空间”本身:建筑变成了一个空壳。在这个空壳里,空间可以直接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功能逻辑来组织。如果技术上可行,资本驱动的空间是可以完全摆脱建筑本身的。 于是,深陷政治和专业双重危机的激进设计小组们决定求助于科学技术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相信极致的科技发展能激发城市和市民的自主性(autonomy)。建筑不再是“大师”或任何权威价值观的产物,而是整体社会环境推动的自主性过程,是每个个体的自由选择的结果——选择城市即选择政治。尽管技术本身是中立的,激进设计项目所描绘的技术却携带着明确的政治立场:极致的技术能诞生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

彼得·库克,“插件城市:最大压力区”,1964 *最后一句话 “...But with all this, there does not have to be monotony. (...有了这些(城市)就不再单调乏味了)” 包含建筑学与政治主张的双重隐喻。

到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电力系统作为技术或许是中立的,但它同时也作为一项基础设施,受到资本生产、政治和文化等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美国广袤的荒蛮之地为基础设施的系统化创造了条件,而欧洲面对的却是历史悠久、布局紧凑的城镇和战争后的满地狼藉。与欧洲政治困境不同的是,美国并没有经历激烈的政治冲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美国社会经济的进步,使之成为了富裕的资产阶级国家新范式。几乎是比喻性地,美国郊区的住宅建筑也完全不同于欧洲建筑,后者深陷现代主义形式风格停滞不前的僵局,而前者仅仅是一个遮蔽各种机电设施的“棚子”: 一座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只要这个棚子能为每个家庭提供了高质量、标准化的生活,大家似乎对建筑师的缺席并没有什么意见。正如评论家雷纳·巴纳姆曾经描述的那样: “美国人既不建造纪念碑,也不建造建筑。” 对欧洲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如果将电力技术视为基础设施,美国和谐的政治环境和快速的社会发展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点。于是为了保持对技术自主性的乐观态度,激进设计小组不约而同地选择进行了“观点清洗”的过程:美国的本土的社会复杂性被“涮洗”出去,电力系统作为一项纯粹的基础设施技术和一种关于民主平等的概念被最终呈现出来。激进设计对于基础设施的观点清洗,是对技术的符号化选择,它把技术从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剥离出来,然后重新嵌入甚至是与之对立的政治话语中。 美国的社会状态和激进设计的“清洗”之间微妙的联系,还可以从超级人工构筑物与荒野的冲突性并置中被反复阅读出来——《无休止城市》的无限结构以绵延起伏的山峦和天空为背景,《超级表面》的连续网格覆盖了沙漠、冰川和火山,穿行在海洋里的《行走城市》等等。对城市和荒野的对峙状态近乎诗意的描绘,是否也是美国正在发生的郊区化进程的映射呢? 到这里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消费主义和基础设施:同样是六七十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个社会现实,同样对激进设计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消费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平等可及的文化,而电力系统及其它基础设施却暗示着隐藏在背后的超级机构。 半个世纪前的激进设计仿佛创造了一个神奇的预言:我们今天就生活在一个没有中心、没有形象、没有质量的无休止城市。当年的激进小组相信极致的技术能产生自主性,相信当技术创新极致到系统自身都无法控制的时候,个体对自我的认知,对权威的反叛,对自由的追求就被激发出来。然而历经二十多年的全球政治动荡,世界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时代,政治、技术与资本的合作反倒更加紧密。我们再次提问:一旦技术被推向极端,系统是否会崩溃,自主性又是否会被唤醒呢?又或者,这座城市永远不会失去控制,而是被隐藏在背后却无所不在的系统支撑着,正如庞大的电力基础设施伪装成一个个小巧的插座,不着痕迹地融入建筑之中。 延伸阅读 Aureli, Pier Vittorio. The project of autonomy: politics and architecture within and against capitalism. Vol. 4.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08. Banham, Reyner, and Penny Sparke. Design by choice. London: Academy editions, 1981. Ambasz, Emilio. Italy: The new domestic landscap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Italian design. No. 15. New York Graphic Society Books, 1972. Branzi, Andrea. No-stop city: Archizoom Associati. Hyx, 2006. Rossi, Aldo, and Peter Eisenman.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2. Tafuri, Manfredo. Architecture and utopia: desig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MIT press, 1976. Lefebvre, Henri, and Donald Nicholson-Smit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Vol. 142. Blackwell: Oxford, 1991. Associati, Archizoom. "City, assembly line of social issues: Ideology and theory of the metropolis." No-stop city: Archizoom Associati. Editions HYX, Orleans (2006): 156-174. The Archigram Archival Project: http://archigram.westminster.ac.uk/ “超表面——地球生活的另一种模式” 视频链接: http://www.architectureplayer.com/clips/supersurface-an-alternative-model-for-life-on-the-earth 作者简介 冯立星,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策展人,上海如恩设计事务所建筑师。 林逸恺,全球知识雷锋知乎机构号运营负责人,日清建筑设计事务所建筑师。 责任编辑 | 郭博雅 王子耕 编辑 | 曹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