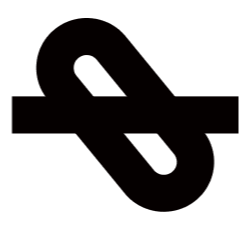激进技术 | 从大字报到小视频:1968年的媒介与空间
一方是街垒、投石、木棒、燃烧瓶,另一方是警棍、子弹、高压水枪与催泪弹。 当美国军队在越南深陷于战争泥潭中时,1968年那场始于学生运动的全球抗争,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式的公开对抗与武力冲突。在1968的一个多世纪前,巴黎这座城市便以拓宽街道、允许坦克开入、防止街垒巷战的原则进行了全面的空间改造。而在五月风暴中,人们开始再次对这座“备战城市”开始了一场自发性的颠覆:课桌椅、铺地砖、甚至连汽车都被掀翻用于建造障碍。讲堂变为了碉堡,广场则被占领为革命的讲坛——仿佛是在贯彻情境主义的宗旨一般,日常的城市经由临时的对抗,转变成了一种战争与事件的空间。

五月风暴中的法国大学校园空间
然而,正如这场反文化运动对后世的影响所证明的,物理空间中的暴力更像是一种宣泄,姿态,随后化为不幸的后果。1968年运动的真正意义,却在于另一种形式的抗争开始:在标语、横幅、影印、照片等传统的视觉媒介以上,随着电子媒体技术的大规模普及,事件各方在信息的获取与传播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从卫星电视、便携摄影、实况转播,到电子扩音器、便携收音机、对讲机、麦克风与直播……正是通过对语言、声音、图像与符号全新的操纵与争夺,68年才获得了比以往革命更为长久的生命力与象征性,甚至反作用于城市空间本身。与同期的实际战争中一样,对物理空间的争夺开始首次转变为一场媒体争夺战,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数字与社交媒体时代。

1967年5月31日,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记者法兰克·雷诺德,从越南进行了一场他称之为“前所未有”的影像播报。他声称,通过电视屏幕,越战将被“带到客厅当中”。

越战作为一场“客厅战争”
与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不同的是,越战成为了第一场通过影像转播直接呈现给大众的战争。相比起报纸上的数字与词语,血肉与硝烟在视网膜上的投影,不仅提供了一种鲜活的感官刺激,更改变了美国大众关于“何为真实”的观念:以电视作为主要消息来源的人数终于超过了报纸。新闻界也开始改变对官方通报与数据的口径依赖,将目光更多地聚焦了身在前线的播报者,以及他们生产的视觉经验上来——信息的流通与权威性已经开始被摄影机与话筒消解。 尽管一线的采访者对电视转播的公平与正义抱有强烈的信心,但发起了越战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却坚持认为,各大电视台的报道包含了强烈的偏见,甚至“受到了越共的控制”。为了同时监控三座电视台的实况播报,他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这间“美国的客厅”中安装了三台电视机,甚至在患胆囊炎入院时,他也一直在病床上关注着电视屏幕。

电视是60年代美国总统获取信息的新窗口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正如1960年的首次电视总统辩论改变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策略一样,由于民众对战争中伤亡越发普遍与直观的感受,对约翰逊与越战的支持率在67年便已跌至反对率以下,早于1968年的越战转折点——春节攻势。媒体的战争已经比肉体的战争早一步探测到了风向的转变。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记者采访越战美军实况
继50年代末苏联、美国相继自主发射人造卫星之后,1962年7月23日,美国、加拿大与欧洲十六国的逾一亿观众,首次通过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发射的电星一号(Telstar)传递的信号,收看了史上首次的跨大西洋电视直播。为了表现这种崭新的、跨越时空的全球连接,屏幕在节目开始被历史性地分为两半——一边是自由女神像,一边是埃菲尔铁塔。大洋彼岸与本地的当下这一瞬间,被并置在了一起。

“电星一号”首次直播中的纽约本地信号,它将与大西洋彼岸传来的信号并列于荧屏上
1967年,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电视节目,在地球上的31个国家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同步直播——通过作为事件的卫星直播,一种普遍的共时性开始在各国居民的心中建立起来。次年,法国左翼青年抗议美国在越军事行动遭到逮捕,引发了一系列大规模学生、教师、工人运动。日本学生打响了第二次反美安保斗争的前哨战,美国的民权运动方兴未艾,意大利各地爆发“炎热的秋天”…… 没有人能够准确地找出68年的核心特质,是反战、民权、教育危机、反文化、性解放、还是少数群体?但可以确定的是,伴随着事件、信息、影像与媒体评论的全球同步,68年所囊括的范围从一开始便也跨越了国界——或许可以说,68年并非由提炼各国的单个事件本身的特质而来,而是由战后第一批全球化的影像媒体与共时化的全球观众所联系在一起的。 正如越战被首次冠以“客厅战争”之名一样,也正是在68年进行了第一波全球实况转播的革命。

对学生们来说,与街道、广场、校园、城市同样重要的,是传单、涂鸦、海报与旗帜。这场以“文化”为名打响的战争,不仅学习了大洋彼岸的大字报与小红书,也吸收了广告、招贴画等西方商业文化作为宣传手段。在巴黎、东京、威尼斯的校园与街头,通过书写、油印、冲洗而被复制、传达的口号与信息,比肢体的暴力与对抗更为长久地留在了今天对这场运动的记忆中。 然而,学生们已经意识到,相比起他们所掌握的几近原始的宣传技术来说,传媒的资源与武器一样,都被收编在国家、机构与集团手中。报纸、广播与电视所能辐射的人群与范围,要远多于有限的都市空间。而与美国的新闻界相比,欧洲的大众传媒要被更紧地握在政权的手中:5月10日,当抗议的队伍从校园涌上街头时,法国政府立刻命令国营的法国广电总局(ORTF)停止对游行进行电视转播。学生们被切断了将影像传播出去的权力。

五月风暴中的讽刺画《你中毒了!》,表现了学生对广播、电视媒体的敌意
运动中的学生大多只能依赖当时流行的便携式收音机,通过欧洲广播一台(Europe 1)或卢森堡广播电视台(RTL)的广播获取运动的最新信息,直到5月23日法国政府屏蔽了短波信号——一部分学生仍能通过对讲机进行联络。法国市民所得到的消息则更加有限:据学者统计,从5月2日到14日间,法国电视台对五月风暴的相关报道仅两个小时,其中一个半小时都是政府公告或警察声明。而即便法国国营广电员工在5月17日至7月13日间,发起了当年夏天最漫长的罢工之一,其结果仍然不算乐观:此间法国对千万工人罢工的电视播报几近为零。 关于五月风暴的电视实况资料,大多来自当时在法的外国记者。尽管基于胶片的手持摄影机在战前便已用于电影的拍摄,但通过电磁信号来保存影像的磁带,却直到1951年才被发明出来。由于录像带可以反复清洗使用,适合电视节目制作,在60年代初,使用肩扛摄像机的外景摄影开始陆续被电视台采用。这种非固定机位的摄制方式可以让外景人员穿梭于人群中进行影像捕捉,其超前性甚至引发了恐惧——早期各种型号的肩抗摄像机多被命名为“移动跟踪狂”或者“变态偷窥狂”之类。但就获得了全新的观察与记录方式的拍摄者而言,比起节日庆典或者体育活动来说,革命与战争都是最适合这种聚焦于当下瞬间的拍摄媒介的非日常场合。

BBC的早期外景摄像机——“移动跟踪狂”
在此前的半个多世纪中,人们曾习惯到电影院观看新闻视频集锦。欧洲最老牌的电影公司——法国百代(Pathé)就一直持续制作新闻电影到1970年为止。五月风暴成为了这种媒介在被电视外景取代前,留下的最后的一批短片之一。然而,经过运送、剪辑、配乐,5月拍摄的新闻短片要一直到当年10月才在电影院上映。相比起来,外景队的录像带只需一天的运输时间,次日即可在电视上播出,卡带随即投入下一轮拍摄。 但即使真实的影像通过电视流出了国外,也无法保证真相能够不带偏见地传播。美国媒体虽对五月风暴进行了大量报道,但却强烈地服务于其意识形态的目的:起初,对学运的关注主要意在讽刺法国政府的无能,贬低戴高乐当局在越战问题上的表现;但在5月24日戴高乐的电视讲话之后,出于惧怕法国左翼运动在国内点燃火种,美国媒体又将戴高乐捧成为社会带来秩序与稳定的英雄。 而在柏林,抗议前一年警方射杀无辜群众的学生领袖鲁迪·杜契克,在德国最大的报纸《图片报(Bild Zeitung)》发表直接仇恨言论后遭保守派暗杀,引发学生前往该报所属的阿克塞尔∙施普林格(Axel Springer)大楼进行围堵。这座欧洲最大的出版集团总部新建于柏林墙边,象征着冷战期间西方意识形态与宣传的碉堡。由于预先得到情报,大楼配置了铁丝网与足够的警力,得以幸免一难。但为了抗议媒体所大规模传播的不实消息,仍有数辆配送报纸的卡车被燃烧瓶焚毁——学生与国家在媒体的角色与影响力上的斗争愈发激化。

如禁城一般受到重重保护的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媒体集团总部
这次“媒体争夺战”的全过程,被女性主义导演赫尔克·桑德(Helke Sander)在同年《打破操纵者的权力!》中记录了下来。但由于施普林格集团的压力,原本准备在电视上播出该片的芬兰电视台不得不雪藏这部作品。在媒体集团这样的压制下,越来越多的文化界从业者开始寻找机会打破机构的控制。1968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与威尼斯双年展都遭到抗议而被迫中止,进步的导演与建筑师们放弃了展出,加入了对学生的声援。 与录像带在电视台外景队中的普及同时,电影人也开始走上街头。便携式摄影机从60年代初起经历了各种技术升级:更轻便的16mm胶片取代了35mm,Éclair 16摄影机集成了同步录音功能,柯达感光度更高的胶片让室内打光不再必需……终于将电影从室内制片场中解放了出来。1968年,从法国的戈达尔到日本的大岛渚到美国的韦克斯勒,新浪潮导演们不约而同地将学生运动的户外实拍片段穿插于电影的叙事中,用一种着眼于瞬时性与当下性的影像语言实现对现实的介入,并对媒介与表现的客观性进行质疑。

戈达尔的手持摄影机
在电视这种即时媒介的影响下,先锋电影人们也开始打破传统的电影生产与叙事。在摄影店的冲印人员罢工的状况下,代表法国电影左岸派的克里斯·马克与《电影手册》派的让-吕克·戈达尔等多名导演共同参与了一个匿名的集体项目——“电影传单(Cinétract)”,其表现的格式是由媒介的特性所决定的:在当时,只要50法郎便可买到一卷100英尺长的16毫米胶片,以每秒24帧拍摄便可得到一段2分50秒的短片,由自己摄影、剪辑、制作,一天之内即可完成。于是,从68年5月起,共计41部“电影传单”短片开始陆续在巴黎各处游击上映,以求最快地反映街头战争实况,对抗国家电视台的转播禁令。

作为一种融合了照片、影像与书写的即时分享媒介,“电影传单”与今天的Instagram小视频并无不同
如果说以今天的视角来看,68年留下的遗产似乎更多地属于“文化”方面,那不过是因为资本与权力已经收编了大部分“非文化”的日常领域罢了。随身携带的收音终端与摄影器材,如同今天的手机摄像头与自制小视频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位于“大厦”内部的传媒集团垄断与诠释事实的能力。

在传统的左派视角中,五月风暴甚至有些过于广泛的学生—教师—工人联盟,由于缺乏政党的领导与统一的诉求,而无法不避免一片混乱的结局。但反过来,在没有集中政党组织的情况下进行了如此大量的动员,在传统的政治实践中也是难以想象的。 在1968年前后的运动中,诞生了一批并不经过事前周密的组织筹划、而是在不断演进的“事件”中崭露头角的学生领袖,其中包括五月风暴初期的象征性人物——“红发丹尼(Daniel Cohn-Bendit)”。他通过接受采访、上电视、以及大规模的露天演说,一面推动抗争的发展,另一面也随着运动的走向而浮沉。

“红发丹尼”在学生中发表演说
从古代的巴西利卡到今天的礼堂与讲堂,由于人声有限的音量,大型的室内空间与完备的声学设计一直都是大型集会的必要条件。而由麦克风与扬声器这一对收音与播放的装置组成的现代音响设备,几乎成为了二十世纪所有政治人物不可或缺的装置:为开国大典特制的“九头鸟”广播,将天安门城楼上的声音传播给了广场上的30万人,而1963年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说,则传递给了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的25万人。 与摄影器材的“上街”与直播技术的实现同步的,是电子扩音器在五月风暴中的使用:它通过一个由电池驱动的放大器电路,将麦克风与扬声器集成到了一件手持器材当中,从而摆脱了传统音响设备所需的空间与布线。这件发明从40年代起在军方中得到应用,从60年代起才取代传统的喇叭筒、开始在一般社会普及。正是它的出现,才打破了身份的壁垒,给了普通人进行公开演说与集结听众的机会。事实上,罗伯特·F·肯尼迪等美国政治人物也是在60年代开始通过扩音喇叭进行街头演讲的。

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F·肯尼迪在街头发表演讲
电子扩音器让广场不再只是示威的舞台,而形成了剧场或讲堂式的“露天的室内”,它既造就了发声的人,也制造了一批聚集的听众。诗人阿拉贡、哲学家萨特、福柯都曾通过扩音喇叭对游行的学生进行声援。随着人的移动而出现或消灭的游击式讲话,也让运动中的组织、动员与走向更加流动及难以捉摸。 在缺乏公共广场空间的日本,继68年的新宿骚乱与69年的东大斗争失败后,抗议者们曾一度聚集在新宿站西出口与室外相连的地下空间里,当时称为“新宿西口地下广场”——虽然名为广场,但实际上只是一条略宽的通道而已。将他们聚集起来的,主要是一些抱着吉他、弹唱反战歌曲的民谣歌手。在流传下来的照片与音频中,他们借助便携式话筒与扬声器,在这个临时的集会广场进行演说,或者通过现场分发的歌词单,与抗议者之间进行你一句我一句的大合唱,俗称“民谣游击队(フォークゲリラ)”。

民谣歌手在众人围坐的中心,通过话筒进行领唱
只有在集体合唱《机动队BLUES》《朋友啊》这样团结性的歌曲时,这个原本有名无实的“广场”才真正获得了它应有的公共性——可惜在立法机构的操作下,“新宿西口地下广场”被迅速更名为“新宿西口地下通道”,从而受到了《道路交通法》的管制。防暴警察立刻以阻塞交通为由,合法地摧毁了“民谣游击队”。建筑空间的性质在一夜之间受到了改变。

位于“通道”与“广场”间的暧昧界限上的新宿西口
事实上,民谣或摇滚歌手在1968年的确扮演着与政治领袖相似的作用。人们通过话筒与扬声器,追求着他们的声音,寻找着交流与认同。个人的声音也被前所未有地放大,吸引着人群与集会。无怪乎,这也是大型音乐节在历史上诞生的时期:1967年6月10日到11日,在伍德斯托克的两年前,幻想博览会与魔山音乐节(The Fantasy Fairand Magic Mountain Music Festival)在旧金山附近举办,开启了当年的“爱之夏”运动。毫无悬念的是,这场美国最初的音乐节的主办者正是旧金山当地的KFRC 610广播电台——通过对音响设备的占有与明星歌手的合作,美国的媒体集团得以成功地引导、并消解掉了数万年轻人的激情与荷尔蒙。 然而,比史上首次露天音乐节上的大门乐队传播得更为广泛的,是两周之后的披头士乐队:在1967年6月25日,在1万名工作人员筹备了10个月,向31个国家的4亿观众播放的首次全球电视直播节目——《我们的世界》结尾,他们现场表演了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之邀、为这次全球同步的人类集会所特别创作的单曲《你只需要爱(All You Need Is Love)》。这个史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通过卫星连线,将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座爱的广场,一场穿透了屏幕的音乐节。

披头士乐队通过首次全球电视节目进行直播演出

媒体、革命、明星——这三者似乎终于在68年,无可避免地纠缠在了一起。约翰·列侬在当年开始与小野洋子密切交往,并写下了《革命(Revolution)》一曲,开始蓄发蓄须,深深地沉浸在嬉皮士式的情绪中。尽管他对“爱”的公开歌颂遭到了不少新左派的反对,但作为媒体的宠儿,他除了与媒体继续互相利用与成就之外,别无选择。 次年,列侬与洋子结婚,并借机召集媒体,预备先后在阿姆斯特丹与纽约进行两次大型的电视蜜月活动——“床上和平”。首先,在阿姆斯特丹希尔顿酒店的702套房中,列侬与洋子在3月25至31日之间,每天从早九点到晚九点接受媒体的直播,然后在5月前往蒙特利尔进行第二次活动,这次录制了著名的大合唱《给和平一次机会(Give Peace a Chance)》。

约翰·列侬与小野洋子的“床上和平”
相比起今天的“网络主播”与抖音快手,约翰·列侬的“床上和平”或许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对私人空间、室内空间进行的媒体直播。当越战的影像通过卫星被传送到每家每户的客厅正中央时,偶像明星的个人生活也从房间内部,被收录到录音带与录像带中,通过大气中的信号在全球传播,并或许比任何游行与学运的影像都要有影响力。1968年的媒体,不仅穿透了物理空间,也改变了室内与室外、私密与公共、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屏幕让客厅变成战场,话筒则让广场变为讲堂……国家、政客、资本、学生、歌手、导演、媒体人,都在试图抓住最新的电子媒介,以期赢得这场媒体战争的胜利。68年的战斗不仅发生在街头巷尾,更发生在信号与影像之间。而对媒体技术的普及与管制之间的平衡,从这时起,便成为了一直延续到今天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问题。

今天网络主播的卧室直播
延伸阅读 Arlen, Michael J. Living-roomWar. (The Television Serie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7. Shiel, Mark. Architectures of Revolt: The Cinematic City circa 1968. Urban Life, Landscape, and Policy.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Gerhardt, Christina, and Sara Saljoughi. 1968 and Global Cinema.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Film and Media Serie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8. 大木晴子, 鈴木一誌. 1969―新宿西口地下広場. 新宿書房, 2014. 作者简介 张微伟,PILLS研究员。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获得媒体与现代性项目认证。研究方向为媒体、影像与城市。 责任编辑 |郭博雅 王子耕 编辑 | 曹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