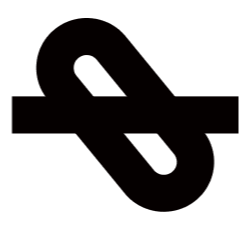激进技术 | 如果技术是答案,那么问题是什么呢——游乐宫与控制论
20世纪中后期,随着战后盛况消退,英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阶层分化逐渐加深,失业人口不断增多,通货膨胀日益加剧。整个社会承受着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冲击与美国大众流行文化的洗礼:电子计算机和航天科技接连问世,电视广播里充斥着甲壳虫和滚石乐队的反叛摇滚,街头出现了独立团体艺术家通俗化的形象。技术与文化发展带来的新奇与迷茫,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1962年,建筑师塞德里克·普莱斯(Cedric Price)与前卫戏剧制作人琼·利特尔伍德(Joan Littlewood)合作,为人们的休闲时光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传统意义的交互建筑——娱乐宫(Fun Palace)。后期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提供的控制论思想和技术支持为二人技术乐观的理想主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整个项目技术的先进性和思想的前卫性,不仅在那个时代,甚至于今天,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图1 1964年游乐宫宣传册海报,塞德里克·普莱斯和琼·利特尔伍德 © CanadianCentre for Architecture

“技术不只是物质表征,也是精神现象。它本身不是外在于文化的,反而正是社会发展中文化作用的要素,是人精神活动的世界。” [1]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西方世界的二十世纪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充斥着战争的硝烟和技术的发展。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在与传统世界决裂,各种思想与理论逐渐分崩离析。战争留下的伤痕,经济的不景气,阶级分化的产生,以及扭曲的消费文化,都令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数字技术发展下,真实与虚幻的界限似乎逐渐模糊,人们心中充满着疑虑与困惑。 承袭于先锋派艺术,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社会文化思潮代表—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1957-1972),在此背景下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新型“文化革命”的战斗旗帜。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于1967年出版的《景观社会》(La Sociétédu Spectacle)中对于“景观 (spectacle)”概念做出了阐述,认为其是一种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表现为一种影像堆砌下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奇观。尽管不可忽略其中左翼思想在社会剧烈变革中表现出的革命激进性 ,但“景观”确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真实的写照:“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积。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2]在二十世纪,尤其是六十年代,人们不再沉迷于商品,而是被景观所迷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由商品消费判定,而是由景观所主导。这里所提出的景观概念,显然是一个批判性的范式,它意味着社会图景是由少数人(资本家、商人和广告制作者)制造出来,由大多数人观看的迷人的过程。对于德波来说,此时人们全都生活在景观的统治之下:“景观不是图像的聚集,而是人们之间由图像所中介的社会关系。”[3](图2)

图2《景观社会》封面,居伊·德波,1967年
思及二十世纪中叶爆发的数字化革命,所谓的景观表象在本质上不可避免的被技术进步所支配。 美国建筑理论家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在1960年《建筑评论》杂志中中对于建筑界未来发展做出的激进预言:“纵观整个世纪,建筑师对于技术和科学概念的迷恋已然脱离了整个文脉背景。当他们依照技术的发展进程而不是建筑师的希冀推进建筑的发展时,他们对此感到无比失望。一代人之前,让建筑师感到失望的是‘机器’,而在不久的将来,取而代之的将是‘计算机’,或者控制论和拓扑学。”[4][y4] 他不仅表露了对科学与技术的偏激运用以及对现代主义建筑师在时代洪流中扮演的角色的担心,或许也暗示了对人类在技术的发展轨道上对个体迷失的忧虑。此时的人们确实被笼罩在一片真实而虚幻的“景观”中,焦虑又迷茫。 此时的建筑界,塞德里克·普赖斯的建筑作品与方法引起了班纳姆的注意。其作品游乐宫背后所阐释的对于技术的态度和文化的倾向显然与提倡技术反对形式的班纳姆对新世纪技术与建筑融合的希冀不谋而合,似乎为当时迷茫的年轻建筑师们照亮了一条出路。

“那些目前在工厂、矿井和办公室工作的人很快就能像现在只有少数人能做到的那样生活: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且用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充实自己的闲暇时间。”[5] ——琼·利特尔伍德 对于二十世纪中叶的英国来说,休闲和娱乐是当时的一个主要问题。随着自动化的普及,战后的工党政府相信在计划得当的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将被稳步消减,未来整个社会的运作模式将会发生改变,将来人们的重点不再是在工作上,而是在休闲娱乐时间上。而游乐宫设计的初衷就是将事物从无限迭代的日常惯例中解放出来,培养一种全新的个性,以打破当下人们麻木的身份认知状态。在设计者的愿景中,游乐宫将作为一种“街头大学”以休闲娱乐的形式给大众提供教育机会。 游乐宫最初的设想是由激进前卫的戏剧制作人琼·利特尔伍德(Joan Littlewood)提出的。二战前,她曾是一家位于曼彻斯特的左派戏剧公司——行动剧院(Theatre of Action)的成员,支持布莱希特美学(Brechtian aesthetics)和街道宣传鼓动戏剧(Agit-prop Street theater)。利特尔伍德的美学特点是强调观众和表演者之间的直接交流,强调身体形式胜于言语的交流。她一直以来的梦想是创造一种新型的剧院:不是由舞台、表演者和观众构成的传统剧院,而是一种纯粹的展现表演和互动本身的剧院。剧院是文化形成的地方,在这里,人们能够作为参与者亲身体验戏剧的变化和更迭。她认为游乐宫概念本身意在创造一种有创造力、有建设性意义的积极娱乐方式。这是一种向英国公众开放的方式,让他们有机会体验新的生活,体验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和互动理念。 1964年,她在《新科学家》(The NewScientist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了对新的休闲社会的期望,并表述了她关于游乐宫的想法——她认为游乐宫是一种新型的“街道大学”。它并不是一个优雅矜持的传统公园,而是未来休闲娱乐设施的先驱:“‘趣味游戏厅’将呈现心理学家和电子工程师为服务工业和战争设计的丰富游戏;知识将经由自动点唱机传播;表演区域将为每个人提供戏剧“治疗”……来自工厂、商店和办公室,厌倦了自己日常生活的男男女女,将能够在这里重现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唤醒对现实的批判意识。游乐宫的本质是随意的:没有什么是强制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在这里发生。这里没有永恒的建筑构造,没有什么能持续十年以上,有些甚至都不到十天。这里没有混凝土体育场,没有污迹和裂缝,没有宏伟的当代建筑遗产,一切都在快速的变化……所列出的区域之间没有明显的划分,整个平面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开放的。” 通过消除工作和休闲之间的传统对立,利特尔伍德试图使娱乐宫发挥其作为大众休闲娱乐场所的民主化作用,允许人们在信奉传统精英主义之外普遍获得属于个人的学习和发展模式。而她对于游乐宫的美妙愿景,显然不可能被传统保守的建筑师所实现,她需要的是热衷控制论、博弈论和计算机等新兴技术,以建筑叛逆者的身份扬名的塞德里克·普赖斯的帮助。

“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享受我们的新自由:如何把机器、机器人、计算机和建筑本身变成获得快乐和享受的工具。” [6] ——塞德里克·普赖斯 普赖斯对技术创新的、不确定的、“计划性过时”的(Obsolescence)建筑想法,与利特尔伍德对另类戏剧实践的构想不谋而合,产生了这个所谓的反建筑项目——游乐宫。利特尔伍德对于戏剧与剧院的追求更加激发了普莱斯的建筑想象力,建筑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建筑师与剧作人共同发展他们先锋概念的工具。 在普赖斯那里,他将游乐宫描述为一个巨大的机械化工厂,所有的建筑构件都通过起重机系统不断地移动,从而完成整个综合体的重置和调整。普赖斯的第一稿图纸(图3)描绘了一个令人费解的三维矩阵的情境:矩阵中到处都是碎片,像是一个永远不会完成的、不断变化的构架。正如普赖斯所说的,“这是一套零件装置,而不是一栋建筑”,班纳姆也认为整个建筑看起来就如同一个“庞大的垂直装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反而实现了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长期以来未能实现的承诺,即一个真正意义上技术成熟的建筑。

图3 游乐宫:室内透视草图,塞德里克·普莱斯,1961-65年 © Canadian Centrefor Architecture
从形式上看,游乐宫既不像传统建筑、也无法构成传统建筑,其本质是一个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的即兴结构框架。这里将要发生的事件,就像这个设计巧妙的装置框架本身一样,并不拘泥于公园里固定长椅一样清晰的空间行为;相反,它更像是一种社会互动实验,可以引发参与者之间的一切相遇与冲突,深入适应社会文化的变化。 普赖斯将其视作一个由多个时间线组成的网络,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空间中协调发展人的不同活动。这里空间的大小,形状和灯光照明等都具有无穷无尽的可控性。在游乐宫的图纸上,其设计集中表现在强调不断产生的运动与它所带来的并置和矛盾,并侧重于创建标准化、模块化的单元,以允许各个组成构件适应项目持续转换和扩展的可能性。游乐宫需要能够“学习”现有的行为模式,并“计划”未来的活动方案。这种操作在概念上涉及到克服装配的机械领域,并需要将焦点由构件组成问题转移到事件组成的交互系统装配问题上。为实现这个不断适应的交互系统,普莱斯希望使用新兴的现代化技术,以开放的、无限期的方案扩大用户使用的可能性和自由度。 起初,普莱斯向他作为结构工程师的朋友弗兰克·纽比(Frank Newby)寻求了帮助,完成了基础“网格服务塔”结构系统的设计。这个服务塔长780英尺、宽360英尺,塔内有楼梯、电梯、电气和机械设备等基础设施,同时包含两台巨型起重机,通过调整整个结构的长度,实现模块的移位和变化。随着项目的逐渐深入,利特尔伍德与普赖斯意识到,游乐宫所带来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仅在于固定结构框架的表层设计,更是广泛地存在于控制论、博弈论和计算机技术的新领域。如果游乐宫能够被建造成为现实,他们需要来自技术领域的各项帮助和支持。1963年初,他们招募大量的人来参与协助这个项目,并成立了一支顾问小组,开始试图深入落实整个方案。各种学科开始联合起来,整个项目的推进变成了建筑、戏剧、技术的综合集成。 [6] 其中被称为“浪漫的控制论领域前辈”的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成为了游乐宫后续发展的关键人物,并开始逐渐将游乐宫的焦点从布莱希特剧场转移到控制论领域。谈及控制论,在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7]之前,它的相关理论通常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相关联,但维纳认为它实际上是一种自然过程的模型,这种自然过程允许所有生物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积极地维持生命的条件。他认为其具有反馈系统,能够使得动态系统实现自我调节和修正,当然这个过程中的核心要素就是“控制”和“信息”,一切信息传递都是为了控制,而任何控制又都有赖于信息反馈来实现。将控制论方法应用于游乐宫的实践之中,对整个项目的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控制论和建筑学的关系要亲密得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哲学理念,斯塔福德·比尔已经证明这个理念就是运筹与优化的哲学。”[8] —戈登·帕斯克 帕斯克带来的控制论技术进展调和了游乐宫项目中建筑实体构件与持续变化的空间事件的关系,让普莱斯与利特尔伍德对科学技术的极度乐观有了安放之处。以控制论为基础的当代人工智能所谈及的人机交互问题,在此时已被这几位对此痴迷的设计师大胆涉及,并试图应用于建筑领域。 在1964年的《对控制论剧院的提议书》中,帕斯克对游乐宫的交互性曾有具体阐述。在剧院中,所有的干预性行为都围绕着两个基本创新议案进行:第一步是设计一个相对简单平价包含按钮和灯光系统的电路,观众可参与其中并收到反馈;第二步则是开发创建交互式脚本的方法和连接戏剧演出的处理系统。他把戏剧脚本的概念与软件部分的设计结合讨论,将游乐宫控制论部分的开发视作一个计算机程序。在这个程序中,观众与演员作为整个戏剧系统的一部分,被纳入程序中考量和计算。帕斯克的图稿(图4、5)令人困惑却又为之着迷,从中能够看出剧院的每个座位都将配备控制装置,以实现观众介入戏剧的演出。而位于后台的计算机将计算观众的行为,输入并将结果传递给舞台上的演员,最终实现二者的互动。

图4、5 游乐宫控制图表(摘自控制论的剧院提议书), 戈登·帕斯克,1964
对帕斯克来说,控制论的主旨是研究复杂的生物、社会或机械系统如何组织和调节自己,从而实现繁殖、进化和学习。他认为控制论不是单向反应的单边系统,而是实体之间的双向“对话”。对他来说,控制论对建筑和设计有着特殊的意义,建筑和设计本质上是人类互动的交互系统,建筑“只有作为人类环境才有意义”。建筑永远与其中的居民互动,一方面为他们服务,另一方面也控制他们的行为。他认为作为包含人类为组件的大型系统的一部分,结构是有其精确功能的,同时有与“装饰性”建筑对比下的朴素性。建筑师主要关注这些大型系统的构建与设计,而不仅仅是水泥砂浆。帕斯克将这种关系称作互利共生(mutualism),指的便是结构系统与或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帕斯克心中,建筑师所设计的结构系统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由于人类的行为变化,不断适应变化并反馈调节其行为的动态结构。他认为建筑师能够通过控制论这个工具进行设计,从而扮演起对社会行为起到控制作用的工程师角色。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普莱斯并不能与他达成一致,他没有迷失在未来科技的浪漫之中,反而清醒地明白其作为建筑师的责任以及当下社会真正的需求所在:控制论系统的作用在于能够使得像建筑师这样的控制力量完全消失,从而让用户能够根据自己的、而不是那些如他一般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意志和愿望,来塑造属于大众自己的环境和空间。此外,利特尔伍德在1964年2月写给帕斯克的文件中也说过:“社会系统的控制分子是在喜悦或悲伤下的行动、意图或变化。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这些信息转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机器只是充当催化剂,大多数的运算是通过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交谈、竞争或合作行为来实现共同目标。”显然她也并不认同游乐宫的设想是在企图控制人们的社会行为。 此处的分歧似乎无碍游乐宫项目的实施推进,但是却反映出控制论技术下人工智能发展于人类的关键问题所在,当代社会人工智能的忧虑在20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已然初见端倪:技术的发展在于解放生产力,协助和帮助人们找寻自我,而不是企图以技术控制社会行为与人类思想。

“游乐宫并不关乎技术,而是关乎于人。”[9] ——塞德里克·普赖斯 游乐宫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民众的质疑以及来自政府的阻碍。为此,普赖斯、利特尔伍德、帕斯克机器团队历经数年,努力化解官僚主义对游乐宫的偏见。但遗憾的是,普赖斯最终还是于1975年宣布这个已有10年历史的项目已经废弃。它的时代已经过去,成为第一个虚拟架构的可能性已然消失。这座游乐宫从未建造过,但多少年来,它一直吸引着建筑师们的想象。这个作品启发了皮阿诺和罗杰斯的巴黎蓬皮杜中心(Centre Pompidou)以及建筑电讯派的插入城市(Plug-in city)(图6)和行走城市(Walking city)等作品和思想;甚至后来,普赖斯也设计建造完成了与之类似的控制论相关建筑作品,但笔者认为这些或表面功夫或浮于幻想都无法超越游乐宫,其思想的超前、对社会的关怀,以及方案深入过程中的碰撞与矛盾都令人神往,然而,人们往往由于对其知之甚少,而产生误解。

图6 插入城市(建筑电讯派档案文件),彼得·库克,1964
事实上,游乐宫不仅仅是人们所理解的纸上建筑或科学幻想,它更是一个真正的项目,一个根植于时代背景下、试图打破“社会景观”所做出的文化尝试与社会创造。普赖斯对于建筑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的态度,并非所谓“建筑叛逆者”的桀骜与不羁,而是一种试图为整个时代的发展变化寻求所谓“连贯性”的勇敢之举。尤其是当他站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交接点上,这种“连贯性”便显得更加重要。 社会中人与人间的互动、人与游乐宫间的互动,是通过数字信息的交互设计得以实现;整个建筑不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功能上,都实现了柯布西耶宣扬的“机器”式建筑。与之相比,现代主义建筑“干净的方盒子”所表达的讯息似乎只算得上是虚张声势的标语与口号。从游乐宫开始,为人们生活而设计的建筑“机器”开始付诸设计。 当然,如果建筑师与剧作人技术乐观的创作设计丢掉了控制论的技术支撑,一切便会显得过于天马行空,甚至仅仅停留在可变化移动构件的建筑结构框架的表层含义之上的纸上谈兵而已。同样,如果没有对于社会环境的思考和人类行为的研究,控制论、博弈论这些技术理论于设计师而言并无裨益。我们无法断言游乐宫项目是科学技术与建筑设计完美融合的巅峰之作,但就班纳姆所意“放弃幻觉主义和机器美学的象征性使用,接受技术不可阻挡的发展”的讯息而言,它绝不失为一次拥抱了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勇敢尝试。 反观步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智能化革命的我们,面对人工智能的强势入侵,必然也应当尝试将其纳入建筑师设计的考量范围。人工智能未来将会与空间结合,使得实体空间技术化。我们无法阻挡数字网络与建筑学的密切交织,新一代的迷茫与慌张,或许与20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并无二致。正如普赖斯所说:“如果技术是答案,那么问题是什么呢?” 注 [1]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中央编译出版社。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著名的德国思想家、经济伦理学家,在伦理经济原理以及市场经济伦理等方面有较深的研究,对我国经济伦理学界有很大的影响。 [2]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 [3] 同上。 [4] The Science Side: Weapons Systems, Computers, Human Sciences. The architectural review. 1960. [5] A labour of fun.Schechter, J. 2003. Popular theatre: A sourcebook. London: Routledge. [6] Cedric Price. A Message to Londoners: draft for a promotional brochure for the Fun Palace, Canadian Centre for Architecture, [7]美国应用数学家,控制论的创始人。著有《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 [8] The architecturalrelevance of cybernetics. Architectural Design, 1969. [9]普赖斯2000年在伦敦接受采访时的内容。 延伸阅读 1. Mary Louise Lobsinger. Cybernetic Theory and Architecture of Performance: Cedric Price’s Fun Palace.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1984-) Vol. 59, No. 3 (Feb 2006), pp. 39-48. 2. JoséHernàndez. From the Fun Palace to the Generator: Cedric Price and conception of the first intelligent building. ARQ (Santiago) [online]. 2015, n.90, pp.48-57. 3. Gordon Pask. The Architecture Relevance of Cybernetics. Architectural Design, 1969, pp.494-496. 4. Gordon Pask. Proposals for a Cybernetic Theatre. Cedric Price Fonds, 1903-2006, Canadian Centre for Architecture. 5.ReynerBanham.Theory and Design in the First Machine Age. Architectural Press, 1960. 6.ReynerBanham. Historian of the Immediate Future[BG7].The MIT Press, 2003. 作者简介 杨晓,同济大学硕士研究生。建筑历史与理论方向。 责任编辑 | 郭博雅 王子耕 编辑 | 丁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