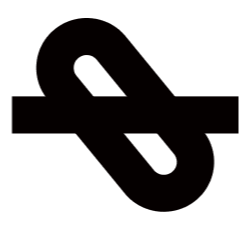激进技术 | 控制论与 “自由的机器” ——水晶球、控制室

Palantír,在托尔金创造的精灵昆雅语中意为“预见”。在《指环王》中,巫师萨鲁曼拥有一件唤作Palantir的魔法道具,形似水晶球,萨鲁曼用它来预见未来,或探查中土世界遥远的地方正在发生的事,又或者用来传递消息。 神话道具Palantír也在当代世界中找到了等价物。2003 年,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 (Peter Thiel) 在把PayPal卖给eBay之后,成立了Palantir Technologies公司。 其早期目标是建立一个超大规模风控系统,基于PayPal上已初见成效的反欺诈系统,来“抗击恐怖主义、保卫公民自由”。Palantir的成立可被视为蒂尔和他所代表的硅谷自由意志主义者对9·11事件巨大冲击的直接回应和对后9·11时代世界秩序的主动构造。Palantir成立之初融资并不顺利,一开始只有蒂尔自掏腰包的3000万美元,后来又获得了CIA旗下风投InQ-Tel的200万美元。运作伊始,Palantir就为五角大楼和CIA服务,分析和挖掘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情报网络收集来的海量数据。Palantir所用模型的特点是能够把大量低相干度的数据类别统合起来,从个体的信用记录、银行流水、位置信息到区域的气候数据、流行病学数据、实时交通数据等,所有可被数据化的真实世界的向度都可以是投喂给Palantir 算法模型的原料。Palantir的主要产品有两个,Palantir Gotham 和 Palantir Metropolis, 前者主要为政府和公立部门服务,后者则销售给私营业主,其名字分别来自于DC漫画宇宙中蝙蝠侠和超人生活的城市。桥水公司利用这些服务协助管理庞大的资产;好时巧克力用Palantir的服务研究消费者行为;Palantir也帮助驻伊美军预测和监控伊拉克各地可能发生的叛乱,甚至还能够规划出特定时间内巴格达最安全的驾驶路线;也有传闻称Palantir参与了追杀本·拉登的行动;在美国本土,移民与海关局和Palantir签署了价值4100万美元的合约,以建立追踪非法移民的数据库。Palantir也为非盈利机构和人道主义事业服务,并往往对此收取较低佣金,项目包括了飓风灾后重建、追踪沙门氏菌疫情、安置叙利亚难民、打击人口贩卖等等。

Palantir Technologies,主营数据挖掘,背景神秘的硅谷独角兽公司
2009年,加拿大网络安全机构 Infowar Monitor 借助 Palantir 的服务追踪到了据称来自中国的赛博间谍网络 GhostNet 和 ShadowNetwork,使得 Palantir 声名大噪。在金融领域,JP摩根的“内部威胁小组” 部署了 Palantir的服务(内部风控在大金融机构非常普遍)。一名退役CIA 特工被雇来领导该小组,利用 Palantir 的技术,监控所有雇员的行动,以防止可能危害公司利益的高风险行为。该小组监控的内容包括考勤纪录、电邮、浏览器历史、打印纪录、公司配给手机的GPS 定位,甚至是电话录音。监控的触角范围不受限制地扩大,直到 JP 摩根的高管意识到自身也成为了监控对象,这一项目才被终止。 Palantir令人警惕的地方并不是它在私营部门的部署,而是它在后9·11 时代政府治理与公民自由的角力中的位置。Palantir 运作的大背景是 2004年,9·11 事件三年后,布什政府通过了“情报改革与反恐法案” (IRTPA) ,其内容之一便是建立一个“信息共享环境”,把“所有相关的联邦、州级、地方实体以及私营部门串联起来”。在2003 年,一项名为“全面信息识别” (TIA) 的政府计划就已经启动,TIA 的指导思想是所谓的“预测性执法” (predictive policing) ,通过收集和分析有关个体的生平信息和数字足迹,预测和制止犯罪,将“恐怖主义”扼杀在萌芽阶段。菲利普·K·迪克1956 年在小说《少数派报告》中构想的司法部“预犯罪科”成为了现实。洛杉矶警局基于预测性执法的理念整合了 Palantir 的服务,建立了一个长期犯罪者清单,每一个被监控对象被分配了相应的长期犯罪分数。然而,这一系统的致命漏洞在于,警察会根据 Palantir 的建议重点盘问长期犯罪者清单上的对象,但每一次盘问又会相应提高他们的长期犯罪分数,和所有其他数据导向的治理体系可能产生的问题一样,这一系统形成了一个不正义的反馈回路。其结果就是有色人种不合比例地成为了预测性执法的对象。上述一系列旨在扩大对公民隐私的侵犯和监控的政策法规不出意料遭到了诸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电子前哨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对,引发合宪性质疑。此种情况下,将公共安全职责私营化(privatiz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成为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策略倾向,诸如 Palantir, i2 Limited, HBGary 等为美国政府、军方和情报机构服务的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公司逐渐壮大,加上美国国家安全局自营的 PRISM、Upstream 和 MYSTIC 等大规模监听计划,其结果是造就了后 9·11 时代的“数字利维坦”,操作于赛博空间和真实世界之间的数字化军事-工业联合体。 创始人彼得·蒂尔的思想背景十分值得注意。蒂尔在斯坦福上学时,结识了在此任教的法国哲学家热内·吉拉德(René Girard),受到了很大影响。吉拉德曾在1966 年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组织了一场名为“批评的语言与人的科学” (The Languages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s of Man) 的会议,邀请了巴特、拉康、德里达等人,这场会议标志着美国人文学界“法国理论”狂热的开端。蒂尔自认为成功地把吉拉德关于“模仿欲望” (mimetic desire) 的理论应用在了投资实践中。2004 年 8 月,蒂尔向当时草创之初、根基不稳的 Facebook 注入了关键的 50 万美元,而这之前一个月,蒂尔在斯坦福参加了一场讨论荣休教授吉拉德的思想与当代政治的研讨会,这些发言后来集结出版,名为《政治与末日》(Politics and Apocalypse)。

彼得·蒂尔,Palantir Technologies创始人
蒂尔不仅资助了这个长达一周的暑期会议,还与一群学者一起参与了会议。在后9·11 时代充满了末世感的凝重空气中,蒂尔做了一场演讲,标题为《斯特劳斯式的时刻》(The Straussian Moment),这是一个稠密而发散的文本,其中他旁征博引,并把重点放在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dt) 和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的学说上。他认为,启蒙理性“削弱”了西方,自由西方对于“民主”和“平等”的教条般的坚持使得它无法回应当下“全球恐怖主义”的挑战,因为“伊斯兰”(蒂尔在这篇讲话中把“伊斯兰”和“9·11 袭击者”无差别地混用)秉持的那种古代的、根本上是宗教的世界观,是当代世俗、理性的西方认为“已经消失了的”,西方因而拒绝承认和回应此种“文明的冲突”。他因循施密特,认为共同体必须依靠“敌我之分”来定义和凝聚。蒂尔在2009 年的文章《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教育》(The Educationof a Libertarian) 中,宣称“已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是兼容的”。在文章另一处,他说,“自1920 年来,福利受惠人群的极大增加和女性获得选举权 —— 两件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尤其难以接受的事 —— 把’资本主义民主’这一概念变成了矛盾修辞 (oxymoron) 。”他接着呼吁,自由意志主义者应当寻求对“政治场域”的超越,他建议了三个新的 “技术前线”:赛博空间、外太空、海洋。在文章的末尾,他作出了安·兰德式的宣告:“这个世界的命运可能依托于某一个人的努力,他建立和传播自由的机器,使得世界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安全的 (the machinery of freedom that makes the world safe for capitalism)。”蒂尔超过一般实业家的制造话语、“微言大义”的能力和在数字新经济中不容忽视的影响力使得他被自由左翼视为强盗大亨 (robber baron) 和邪恶思想的传播者,被保守主义者则视为“哲人王”一类的人物。虽然这套叙事并未与后 9·11 时代十分流行的、高雅或通俗的各个版本“文明冲突论”有多大区别。 值得额外笔墨的是,Palantir 这样一个巨大而缜密的“装置” (dispositif) 与其创始人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这套装置的运行机理和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是否存在某种根本矛盾?对当代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Palantir 这类本质上是中心化的大数据治理术,跟最广义的计划经济(包括但不限于苏联中央计划模式)的关系是什么?从表面上看,Palantir 毫无疑问拥有更高的算力、更先进的模型、对现实刻画更准确以及来源更广的数据(大部分数据却是源于政府机构和公共机制),但是这无法将它和(中央的或分散的、历史上的或理想中的)计划者作本质区分。有证据表明,类似Palantir 的一个或多个系统在太平洋对岸早已在难以估量的巨大尺度上、在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上运作。对于蒂尔来说,用类似 Palantir 的大数据治理术回应“敌人”的挑战,进行“敌我”区分,巩固“资本主义”的运作,这样换来的“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吗?又或者他想保卫的只是富豪统治 (plutocracy) ?Palantir 在何种意义上是他口中的“自由的机器”而不是其对立物?蒂尔对此给出的一个辩护是“智能的侵入意味着更少的侵入” (smart intrusion means less intrusion),因为在反恐战争中“政府收集了他们无法处理的海量数据,如果我们能帮助政府理解这些数据,那么就可以终止无差别的监控。” 当然,人们可以辩护道,Palantir 事实上运行在一个极端青睐自由市场的政体之下,并且它所依赖的诸种计算技术正是自由意志主义者推崇的自由市场和“企业家精神”的产物。然而,暂且不论此种说法忽略了20 世纪计算技术的战争源头,即政府与军方占支配地位的资金投入和组织努力。如果我们深入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技术史,尤其是各种形态的社会主义计划对计算技术的构想和部署,我们将会发现社会主义理想与计算技术之间的暧昧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天然的亲和力。 让我们回想 20世纪 20 年代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社会主义计算问题之辩”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经济学家纽拉特(Otto Neurath) 在一战时参与了德意志帝国战时经济计划的制定。他在实践中观察到,在战争动员中,国家作为中央计划者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的计划手段,既保证了必须生活物资的供给,又最大化了军工产出。1919 年,他写作了名为《战时经济》 (War Economy) 的小册子,其中他推想,类似战时动员的国家经济计划也可以在和平时期使用,并也许可以比自由市场更高效。这一构想引起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和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 的注意,他们对计划经济的构想做出了缜密的批评。 哈耶克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是一针见血的。他精准地认识到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由市场和计划经济两种模型中“知识”的问题。市场中的理性行动者拥有各自局域性的知识,并且可以根据自身的偏好在价格变化中做出相应的反应,而交易的行为就是信息的传播和扩散。这样一种“知识”是弥散在市场中的,类似于某种分布式智能 (distributed intelligence)。而中央计划者试图通过抽样的统计数据获得某种关于经济的总体性“知识”,并以试错的方式设定物资的价格和供需,这样一种中心化的“知识”与分布式的“知识”的总和无法比拟,因为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获得关于市场的全部信息。“我所关心的知识正是在本质上无法进入统计数据,进而也就无法以统计表格的形式被传达给某个中央权威的那种。”(哈耶克,“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1945)这种难以被表征的知识类似于迈克·波兰尼 (Michael Polanyi) 所说的“隐性知识” (tacit knowledge),也可以被理解为“具身知识” (em-bodied knowledge)。 在波兰尼举的关于隐性知识的例子中 (The Tacit Dimension, 1983),一个典型就是人脸识别问题。人类可以在数千张面孔中找到她想找到的某个面孔,但却无法用语言精确描述是何种特征将这个面孔与其他区分开来;或者又像骑自行车,习得了这一技能的人无法仅仅通过语言文字就把“诀窍”传授给不会骑自行车的人。在哈耶克描绘的图景中,市场的有效性正是依赖于一个个具备了隐性知识的单子对这些知识进行符合自身利益的灵活运用。 再后来,原本平行的社会主义思想脉络与计算史、人工智能的历史产生了交汇点。20 世纪中叶,试图以符号逻辑达成通用人工智能的努力屡屡碰壁,而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复兴的机器学习范式恰恰擅长在具体问题中捕捉这样一种难以言说的知识。当适用于小领域的专门设计的算法被投喂了海量带标注的数据,其给出预测的准确性可能超越人的认知限度,另外基于无监督学习的数据挖掘还可能发现人类过往经验之外的向度。 十八世纪末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是为帮助理解一个被蒸汽机搅动的世界。中央计划和自由市场之间孰优孰劣的论争不断得到更新,20 世纪后半叶的历史似乎是证明了市场主导的优越性。但柏林墙倒塌30 年之后,这个经验答案也开始显得陈旧起来。“AI 将会带来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是否应当严肃对待最近几年这一声势渐起的的宣告?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过去,20 世纪60、70 年代发生在全球南方、代表着高峰现代性的诸多技术事件会告诉我们,技术是“姓社”还是“姓资”,是“先进”还是“落后”,这些二元对立并不如看上去那般泾渭分明。通过考察这些事件我们可能瞥见全球技术史进程的众多歧路,那些似是而非的“此路不通”,以及我们现已失落的未来。

1973年 9 月11 日,一场军事政变席卷了智利。走社会主义路线的民选总统阿连德 (Salvador Allende)被陆军总将皮诺切特 (Augusto Pinochet) 在内的亲美右翼军人推翻。在叛军的围攻下,阿连德同警卫队在短暂抵抗之后,在总统府 La Moneda 饮弹自尽,洞穿其头颅的子弹来自于好友卡斯特罗赠予的步枪。之后一年内,皮诺切特逐步掌控了局面,建立起智利历史上最血腥的军事独裁政权,结束了智利自1930 年代起未曾中断的民主选举传统。 1971年,在政变大约两年前,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计划曾试图把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智利带入计算机时代。这一计划被言简意赅地命名为“赛博协同” (Project Cybersyn)。1970 年,阿连德领导的人民阵线联盟在一场由三方角逐的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赢得了大选。入主总统府之后,阿连德着手推行一项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其内容包括了国有化铜矿业和银行业、建立公立医疗和教育系统、土地改革等等。智利的铜储量占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对铜矿业的国有化从50 年代就开始了,但在阿连德任内才彻底实现。这一过程中,智利本土企业所拥有的矿井不受影响,而被褫夺所有权的主要是由美国公司所拥有的三处储量最大的铜矿。因为这一“维护主权的行动”和社会主义路线,阿连德政府遭到了美国的经济制裁和禁运,加速了国内左右对立和经济恶化。 “赛博协同”项目的运营主管艾思帕赫 (Raul Espejo) 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阿连德之前的社会主义政权,如苏联和古巴,其中央计划经济模型要求成百上千万人无条件服从由一小撮专家和技术官僚组成的“计划机器”的指挥。而在智利,其悠长的代议制民主传统与此种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模型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中,“赛博协同”项目应运而生了。在阿连德政府组建之初,智利国家发展局(CORFO)的年轻官员弗洛雷斯 (Fernando Flores) 在阿连德的民主社会主义理想和当时方兴未艾的控制论思潮之间找到了融汇的可能。控制论,一个二战期间诞生的新兴学科,脱胎于维纳 (Norbert Wiener) 在自控防空火炮研发中遇到的问题,最初旨在研究动物和机器在一定环境下的自动控制和自我调节问题,后来很快扩散为一股跨学科思潮,也成为思考社会系统的一个框架,被战后的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挪用和壮大。而让弗洛雷斯兴奋,并感到能在智利大有用武之地的,是由英国控制论专家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 开创的管理控制论 (management cybernetics).

图1 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图2 英国控制论专家比尔(右)在智利。
比尔不太像是一个社会主义同志,他曾经是英国最大的钢铁公司联合钢铁的高级顾问,在英国过着奢靡的生活。1971 年7 月,弗洛雷斯向比尔发送了邀请,请他来智利主导一个大胆的实验,利用他的控制论知识和在大机构做运筹顾问的经验,为整个国家建立一套全新的组织和通信系统,既要能统筹和计划正在国有化进程当中的智利经济,又要为工人自主决策预留下可能。对比尔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可以在国家级别的庞大尺度上试验和改进他的理论,因此他欣然接受。在比尔到来之前一段时间,CORFO 的精力主要花在建立国有化的轻工业上。比尔到来之后,他提议工作重心应当转移到把整个工业经济作为复杂系统处理,改进其内部调控与通信。“赛博协同”项目的成员开始集中研读比尔1966年的著作《决策与控制》(Decision and Control),以及他带到智利的、即将付梓的书稿《公司之脑》(Brain of the Firm),其中他阐明了管理控制论的基本原理。比尔最重要的理论模型是“活性系统模型” (Viable System Model, VSM)。他受人和动物的神经系统启发,提出了一个五个层次的递归和嵌套模型,来描述具有适应环境和自我调节能力的系统。对应到赛博协同项目与智利工业经济,这五个层次由上到下分别为:CORFO;其下属四个“rama” (部门);每个部门有一系列工业委员会;每个委员会下辖众多企业;每个企业拥有数个工厂。

比尔的活性系统模型
在到达智利不久后,比尔草拟了一份工作计划,其核心是建立一个处理智利工业经济数据的算法,或者说赛博协同项目的“软件”,命名为 Cyberstride。除了弗洛雷斯在圣地亚哥本地组建的团队,比尔还在伦敦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召集了一批数学家和程序员,基于贝叶斯方法搭建该算法模型。他自己则几乎停掉了同期在英国的顾问工作。 地理上,智利是一个南北跨度 4000 多公里,东西平均跨度只有200 公里的狭长国家。同时,尼克松政府为了防止拉丁美洲另一个古巴的出现,发起了对阿连德政府的制裁,并支持智利国内右翼进行对抗和破坏。在有限的技术、地理条件及国际封锁、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实时地从各地工厂获取生产数据是一个十足的挑战。碰巧,赛博协同项目小组在一家国有工厂发现大量闲置的电传机 (telex machine)。电传机在二战后到八十年代传真机流行之前十分常见,是一种基于文本的商务通信方式,由电报系统发展而来,采用二进制编码,有独立于电话机的网络。考虑到电传机在各大工厂、工业委员会和政府机关普遍安装,比尔决定基于现有电传机网络来搭建赛博协同项目的通信系统,命名为Cybernet. 项目组在 CORFO 大楼的一个房间里安装了几十台电传机。全国各个企业和工厂将数据汇总到这里,再由 Cyberstride 进行处理。Cyberstride 以租用计算时间的形式运行在一台 IBM 360 大型机上,这是当时团队所能申请到的全部算力。但由于智利当时一共只有3 台 IBM 360 系,以及不到 50 台美国公司在 60年代引进的中小型机,在众多政府项目算力需求的拥堵之下,赛博协同项目的计算时间无法得到保证。在项目后期,实时数据处理已变得不可能,延迟一度超过了48 小时。

图1 电传机。图2 IBM 360大型机 (1965年发布)。
在 Cyberstride和 Cybernet 的基础上,比尔还希望搭建一个基于过往数据模拟和预测智利工业经济走向的模型,命名为 CHECO(CHilean ECOnomy), 它还有一个别名叫“Futuro.” 一群智利经济学家在伦敦的系统动力学家们的帮助下搭建了 CHECO的初始版本。这个动力学模型使用了 MIT 的杰伊·福勒斯特 (Jay Forrester) 主持开发的 DYNAMO 编程语言。该语言在当时的系统动力学模拟中十分流行,正是用它编写的 World3 模型在罗马俱乐部 1972 年的有争议著作《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Growth) 中给出了关于人口大爆炸导致资源枯竭的悲观预测。到政变之前,智利工业经济27%的实体已经被纳入赛博协同项目。 为了维持政府高层的注意,1972 年,赛博协同项目小组在国家电信公司大楼的中庭搭建了一间未来感十足的“中央控制室” (Opsroom),由德国左翼设计师居伊·彭瑟佩 (Gui Bonsiepe) 领导的团队设计。尽管这间控制室直到政变之前都只是作为一个原型或“样板间”存在,并未真正投入使用,它还是因其大胆前卫的视觉性和暗含的潜能成为了赛博协同项目最为偶像化和广为人知的符号。控制室呈六边形,直径大约十米,装有几组投影屏幕和七个玻璃钢制成的转椅。转椅围成一个圈,没有明显的等级感。控制室内的决策者可以通过转椅上硕大的按钮切换显示 Cybernet 收集的各项数据和 Cyberstride 识别出的趋势,抑或是 CHECO 模拟器对未来经济数据的预测。在比尔的设想中,等到赛博协同项目完成时,每一个工厂都将拥有类似的控制室,坐在转椅上的决策者除了政府官员,更可能是普通的工厂工人。比尔将中央控制室称为“自由机器” (Liberty Machine),它既是一个人机交互界面,用机器和信息的力量帮助决策,又是一个促进决策主体平等参与的物理空间。(参见王洪喆《阿连德的大数据乌托邦》)

赛博协同项目中央控制室
1972年10月,在恶性通胀、生活水平下降和右翼策动之下,智利全国的卡车司机和个体商贩进行了大范围的罢工。弗洛雷斯及下属此时利用赛博协同项目的电传机网络,统筹全国的工厂,工厂之间也利用这一网络分享燃料和运输工具。此次罢工逐渐平息,而赛博协同项目的声望大增。同年12 月,阿连德参观了中央控制室。1973 年 9 月 8 日,阿连德殒命之前三天,他还指示赛博协同项目小组,将中央控制室搬迁至总统府内。

图1 中央控制室局部。图2 中央控制室的转椅,由Gui Bonsiepe设计。
在赛博协同项目投入使用之前,阿连德的政权首先倒台了。将军皮诺切特不需要控制论加持的中央计划经济,他将用暴力让自由市场重回智利。在阿连德上任之初,周恩来曾发去贺电,除了赞颂阿连德通过民主选举给智利带来社会主义以外,也提醒了阿连德“枪杆子里出政权”、武装保卫社会主义果实的必要性。但智利的情势显然与中国不同,在冷战阴影之下,要在美国的后院,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阿连德可能没有太多选择。 1973年的政变深深震动了比尔,他回到英国后,花了许多精力来拯救流亡的智利同事。他没有回到过去奢靡的生活,而是住在威尔士乡下一个不通电话的小草屋。这期间,深受控制论影响的音乐人布莱恩·伊诺(Brian Eno) 拜访了比尔,还把比尔的书赠予了大卫·鲍伊(David Bowie)。在比尔的余生中,他尝试在其他地方,如乌拉圭、委内瑞拉、加拿大重复类似赛博协同项目的试验,但都没有成功。 有趣的是,蒂尔和比尔在想象自己的发明时,都借助了“自由的机器”这一隐喻,并都认为自己手中的“装置”将传播自己认同的理念。在真实世界中,他们的发明同“自由”之间却展示了复杂而微妙的矛盾,要想传播“自由”,也许首先需要跟“自由”的对立面共谋:比尔梦想中的计划无法脱离与政治强人合作,而上篇中蒂尔的“水晶球”则可以说肇始于反恐战争中为全面数据采集开绿灯的“爱国者法案”。 为了给这样一类装置在媒介史中定位,让我们回到这一切的另一个源头,即维纳在 MIT 的同事、克劳德·香农的导师凡内瓦·布什(VennevaBush)。1945 年,时任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 (OSRD) 主任、领导六千名战争科学家的布什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文章《诚如所思》(As We May Think)。在这篇传奇文章中,布什构想了一种设备/装置,他命名为“memex”,可以储存、检索、分析和传递人类的集体记忆与集体知识。为实现这些功能,布什当时提议的技术主要是高分辨率微缩胶卷、投影屏幕和干板摄影等。他想象,有了这样一个设备,一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可以被缩小到火柴盒的尺寸,而藏书百万的图书馆可以被压缩到一个书桌里。布什在《大西洋月刊》1945 年7 月和 9 月先后发表了这篇文章的长短版本,时间恰好是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前与之后。这篇文章影响深远,1995 年在 MIT 召开的《诚如所思》五十周年研讨会上,诸如万维网的发明者 Tim Berners-Lee, 人机交互的奠基者、鼠标的发明人Douglas Engelbart, 超文本 (hypertext) 概念的提出者 Ted Nelson 等等信息技术领域的标志性人物纷纷发言,谈及布什这篇文章对他们的影响。

图1 赛博协同项目总图示。图2 memex机器示意图。
比布什构想的设备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勾勒的人类知识图景的转变。在《诚如所思》中,布什开宗明义地讲道,“这不是一场科学家的战争;这是一场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战争。” 他所忧心的世纪中叶的人类危机有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导向大规模毁灭而不是对人类知识与记忆的重新结构;二是信息爆炸以及随之而来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导致了不同学科之间日渐扩大的界限和藩篱,知识的总量已经大大超过了个体的认知限度,为进一步挖掘知识,各个学科必须保持自己既定的轨道,继续深化各自特异的知识形式、方法和技术。布什的提议正是想要通过克服人类记忆的局限来实现知识图景的变革,实现从信息爆炸到知识爆炸的转化。尤其值得揣摩的是,产生第一个问题的那种状况可能恰恰是解决第二个问题的钥匙。世纪中叶的美国,国家机器全力驱动的战争机器带来了一种知识的例外状态:军工研究本质上跨学科协作的要求和战争动员令的不可违抗性促使不同学科的专家尝试弥合学科之间的界限并建立切实有效的合作关系和可转译的话语管道。这种打破学科界限的努力不仅仅发生在科学界内部,还发生在C. P. Snow 所说的“两种文化” 之间,即科学与人文之间。 控制论就是这样一个战争机器拆除学科边界的过程中诞生的具有代表性的新思潮。“跨学科性”这个今日学术界常见的时髦口号在当时还是生造不久的新词。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规训”与“学科”就是同一个词(discipline)——二者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可以进行微妙的互换,这种句法上的同一和语义上的二重性直接导向了我们在此处所采取的将“规训社会” 与“学科社会”等同看待的这一视角。规训社会中封闭围栏的瓦解与学科社会中学科边界的模糊是同一个进程的不同面貌。 德勒兹在《控制社会后记》(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中勾勒了从福柯勾勒的规训社会到他所言的控制社会的转变。在规训社会中,我们从一个封闭的围栏进入另一个封闭的围栏,从家庭到学校,军队到医院,工厂到监狱。而世纪中叶战争机器带来的例外状态摧毁了科学家习以为常的学校、各学科实验室及工业界的边界,取而代之的组织形式是更高优先级的情报网络、军事层级、命令与控制链条。德勒兹认为,在控制社会中,前述规训社会的封闭空间互相连通了,取代各个封闭空间中“规训”过程的是一种普遍的“调制” (modulation)。例如,在离开学校之后,教育并不会就此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培训”。德勒兹转述了瓜塔里所举的一个例子,在城市中生活的某个人拥有一张门禁卡,借助这张门禁卡他可以进出自己的公寓、办公室,因为这张卡可以刷开指定的闸机和围栏;但真正重要不是那些闸机和围栏,而是追踪他行踪的计算系统,因为这套系统可以随时取消他的权限。福柯描绘了规训权力取代主权权力 (sovereign power) 的图景,而德勒兹提醒我们,在控制社会中,主权权力随时可能改头换面而复归。比尔和蒂尔各自版本的 “自由机器”难以处理的正是装置(机器)与主权权力的关系,尽管比尔失败了,蒂尔暂时成功了。假设比尔的计划成功了,那又是怎样一种社会形态?一左一右两种生发于不同时空、带有不同终极目的 (telos) 的控制论-社会-经济-政治实验,二者搭建的装置结构本身却是惊人地相似。 在控制社会中复归的主权权力,显然不再简单是《利维坦》中描绘的那种人们通过签订“社会契约”,将部分的个体权利让渡给一个自然人代表的绝对主权(王权),以避免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中。显然,在这样一套数字治理的框架下,不再需要推举出一个自然人来代表订立契约的个体意志总和——甚至不再需要对这样一个主权人格化——像《利维坦》封面所绘的那样。德勒兹在不同社会形式与其中机器的形态之间建立了某种对应,王权社会拥有简单机械:杠杆、滑轮、时钟;规训社会对应的是热机,它的被动风险是熵增,主动风险是“被破坏”(如卢德运动);而控制社会对应的则是控制论机器(计算设备),它的被动风险是“宕机” (bug),主动风险是盗版和病毒等等。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决定论,因为机器可被视为编码了其所处社会的社会关系总和。控制论机器的危险在于反馈回路在本体论层面蕴涵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彻底拒斥,反馈回路是没有真正的外部性的,或者说它并不预设存在无法被纳入反馈回路的外部,它也因此无法导向替代性的或更高层面的现实。反馈回路是高度可塑的,系统的稳态 (homeostasis) 通过普遍性的调制得以实现,它与历史终结论高度同构。面对目前统治我们的“数字利维坦”,即便此刻我们神秘地唤出犹太教泥巨人(Golem)的典故,或者弗兰肯斯坦博士的故事,谴责凡人僭越造物主一角的狂妄自大,此种后见之明也都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在控制社会中,想要做一个“电子卢德分子”显然比在19 世纪捣毁纺织机器在技术上困难得多,控制论机器加持的主权权力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力量平衡被剧烈打破了,我们急需一个由技术武装到牙齿、高度匿名、弥散和去中心化的新骇客-公民阶级,来与技术官僚制和控制论机器抗衡。用唐娜·哈拉维的话说,“二十世纪晚期的机器已经彻底模糊了自然与人工之间的区分,模糊了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区分,模糊了自我开发与外部设计以及其他许多曾适用于有机体和机械的区分。我们的机器生动得让人不安,我们自己却死气沉沉得让人恐惧。” 作者简介 冯骏原 | 工作在上海的艺术家、写作者。 责任编辑 | 郭博雅 王子耕 编辑 | 曹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