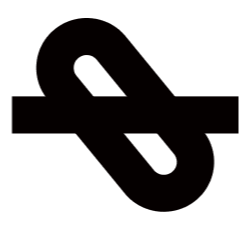激进技术 | 激进技术与“1968”的周期(下)

二战后至七十年代,是“1968”结构模型的全面形成。同上一次一样,首先是资本主义内部理性化激进技术的疯狂积累,然后是文化激进技术在全球社会领域的集群发生,以及两者之间持续近十年的震荡性角逐。

1948年4月3日,杜鲁门签署了马歇尔计划(EuropeanRecovery Program)。战后,美国工厂又很快转入了民用生产,物资供应爆炸性增长,长期的繁荣需要有输出这些商品的市场,欧洲就成了这些商品输出的最佳选择。而事实上,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中的很大一部分,正是这些来自美国的工业品和原料。

马歇尔的欧洲重建计划的宣传海报(1948-1952),以及马歇尔计划在欧洲重建过程中的资本投入。美国资本携带激进技术,重新建造了二战后的欧洲。

图1 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是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变得如此不同,如此迷人?》(JustWhat Is It That Makes Today's Home So Different, So Appealing,1956) 。 图2 伦敦白教堂画廊“这就是明天”(This is Tomorrow exhibition installation, Whitechapel Gallery, 1956)。这个展览可以被理解为马歇尔计划的欧洲日常生活后果。激进技术催生了乐观主义。汉密尔顿于1990年讲述了他创作该作品的动机:“这件拼贴画在‘这就是明天’这样一个试图囊括正在朔造着战后英国走向的各种影响的说教式的展览中,扮演着一个说教的角色。我们似乎正在走向光明的未来,我们以星空般的信心拥抱变化万千的高科技世界。乐观主义的巨浪将我们带入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1945年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重构,欧美社会在生产、消费与居住三个领域都产生了激增性的发展。在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下,美国重新主导了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世界的秩序与重新结构化,特别是重新布局了全球的金融结算系统,美元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贸易发展的内在标准。战后重建实际上使美国将福特制大工业生产方式,扩展到美国、欧洲乃至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空间,从而在大尺度范围内,以创造性破坏的方式标准化改造了资本所能触及的所有土地(即“激进”的彻底性)。很快,作为激进技术最典型代表的美国军工技术,主导了整个欧美生活日用品世界,使得整个社会成为了一个工厂。到了五十年代晚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全面进入富裕社会。大工业生产技术为资本主义带来了繁荣,但随即也带来了危机——福特制生产方式的高速积累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浮出水面,迫使消费取代生产,成为推动资本继续积累的下一个动力。但是,与匮乏时代的强迫性生产性技术相比,富裕时代出现的是大众的自愿性消费技术,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于是,与商品推销有关的一系列广告术与洗脑术发展起来。比如在美国,整个国家都卷入了对全体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重塑。信息与符号技术正是在这种需求下快速发展起来,也就是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六十年代初所说的媒介时代的来临。符号技术最为重要的功能在于——通过给工业生产出来的标准化产品赋予表面上差异化的符号,制造出事实上无限多的多样性,从而实现商品流通总数量与总体量上的无限积累。与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消费技术相比,反资本主义的美学技术发展有限。比如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基本上沦为抽象商品逻辑的图解,或者沦为设计领域的形式资源库,失去了对社会的批判作用。五十年代兴起的波普艺术一开始对精英艺术有批判性,解放了艺术与大众之间的连接能量,但很快就沦为商品景观的差异符号。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就将自己的工作室称作“工厂”而非工作室,他提供的不是艺术作品,而是一套“生产策略”——一套可以帮助资本主义商品打扮自己的化妆术。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与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政治经济领域的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与军工技术领域的维纳的控制论(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1948)具有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关于驾驭规模庞大的复杂系统的理论,即,是关于“系统的系统”的理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规模的扩大使得计划与市场、控制与不确定性之间需要辩证性的结合,以及需要现实可操作的机制。这些理论的正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
与经济领域发生的巨变相伴随的,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技术的不断提升。由于经济总量、人口、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管理的问题日益变得重要,这就导致为了精确管理这个庞大规模所需要的标准化进程。于是,战争中逐渐发展出来的控制论技术逐渐与国家治理技术相结合,力图在总体上实现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可控性与可预测性。这些管理技术反映在经济领域、城市化领域与高等教育领域,使得社会日益单一化。虽然大众拥抱经济增长,但社会结构如果不能跟上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出现问题(特别是在如何平等分配经济发展红利以及边缘群体的文化身份等领域上)。这些问题的后果,在美国、法国的凯恩斯主义治理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凯恩斯主义提升了国家对于经济的整体介入程度,使得计划与市场严密结合,但就在它带来战后黄金20年,即发展到自己顶峰的时刻,它内在的矛盾也在不断地积累。这种在文化领域、社会领域的累年欠账在1968年集中、系统性地爆发了。
![“红旗悬挂在工厂上空,抗议者高唱《国际歌》,革命口号装饰在海报、横幅与墙上:‘直到最后一个有着官僚内脏的资本家被绞死,人类才会快乐’。” —1968五一宣言(May Day Manifesto 1968,Edited by Raymond Williams)[[1]]](https://pills-static.oss-cn-beijing.aliyuncs.com/uploaded/pills/research/content/2024/11/26/av9iut0zv0c.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3000,limit_0/format,jpg/interlace,1/quality,Q_100)
“红旗悬挂在工厂上空,抗议者高唱《国际歌》,革命口号装饰在海报、横幅与墙上:‘直到最后一个有着官僚内脏的资本家被绞死,人类才会快乐’。” —1968五一宣言(May Day Manifesto 1968,Edited by Raymond Williams)[[1]]
1968年的种种社会动荡和文化事件表面上看发生得突然,实际上恰逢其时。“1968”是战后资本主义福特制生产达到最高峰的时期,也就是即将面临产能过剩的前期,内部/外部同时出现的一次暂时调停,它像一个泄洪口一样,将积累的矛盾以资本主义能够承受的方式提前释放了。或者说,“1968”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在经济理性化与政治科层化激增后,其带来的社会矛盾扩张到无法弥合的程度,从而在社会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激进调停。[[2]]

1968年“五月风暴”,法国巴黎。

图1 阿波罗8号登月计划(Plan of the track to the Moon followed byApollo 8)。 图2 地球升起-阿波罗8号机组人员。四张照片,1968年(Earth rise — Apollo 8 crew. Four photographs, 1968.)。
![阿姆斯特朗(ARMSTRONG, Neil ,1930-2012)签名照片,[肯尼迪航天中心,1969年6月19日]](https://pills-static.oss-cn-beijing.aliyuncs.com/uploaded/pills/research/content/2024/11/26/8pne61tcb0q.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3000,limit_0/format,jpg/interlace,1/quality,Q_100)
阿姆斯特朗(ARMSTRONG, Neil ,1930-2012)签名照片,[肯尼迪航天中心,1969年6月19日]

1968年《全球概览》首期封面与目录。这个目录所显示的主题——理解整个系统、庇护所与土地实用、工业与手工业、信息交流、社群、游牧、学习,精确的抓住了这个时代的技术与社会的关键议题。一方面,《全球概览》把资本主义的整体系统进化、高度发达的军工技术巧妙的隐含在地球美学的图像之中,另一方面,显示了这个系统之下,个人利用技术的双向度机制所能展开的潜能。
从事实来看,六十年代经济生产领域的产能过剩压力,是通过两种方式集中表现出来的。对内就是社会危机与文化危机,对外就是通过战争政治与太空技术来消化过剩资本。前者如法国版本,后者如美国版本(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其他国家,大都在这两个版本之间)。[[3]] 当然,更无法忽视的原因是,反资本主义的激进技术经过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发展,至少在文化与社会领域,已经积累到与可以与资本主义进行抵抗的程度。引发“1968”反资本主义的文化激进技术,正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内部同时发展起来的,因此这次文化激进技术的重新兴起在三个层面意义重大。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1964)。这本书可被理解为对战后资本主义激进技术意识形态本质的分析。技术无法是“中立性”的概念,它“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与逻辑中已经起着作用……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马尔库塞的分析可以作为六十年代意大利建筑视窗小组“无止尽城市”理论项目的意识形态批判图解。
第一,“1968”在意识形态维度,继承了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遗产,特别是吸收了大量20世纪前期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多思想。1964年出版的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从意识形态维度充分揭示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的极权本质。在马尔库塞看来,在新的控制形式下,极权逻辑超越了以往的简单暴力镇压方式,允许社会拥有反对面,但这种反对面是假的,只会在不触及制度本质的前提下被允许,以至于整个社会都成为了单向度的存在,即一个被彻底格式化的社会。同样1967年出版的德波(Guy Debord)的《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spectacle),则对资本主义正在兴起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做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商品的符号景观已经超越商品本身,成为了异化所有大众的新工具。实际上,马尔库塞与德波,分别从生产与消费两个角度,理论化了“1968”的结构模型。

图1 情境主义国际,比利时,1962年。以德波为核心的情境主义国际的成立与解散(1957-1972),可被视为战马尔库塞所说的发达工业社会内部抵抗。情境主义国际继承了20年代历史先锋派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立场和美学形式语言,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辩证性吸收,情境主义重塑了艺术和政治的社会介入实践。 图2 国际情境主义的12本期刊(1958年6月至1969年9月)。通过对黑白照片、卡通画与插图等大众媒介的引用,情境主义的理论文献扩展出改造社会的能量。
第二,“1968”在形式语言维度,继承了20世纪早期诸多艺术成果,从而在文化领域——不同于大工业物质生产的非物质生产领域——占据了话语权。反资本主义的激进文化技术一方面从历史先锋派那里继承了左翼价值立场,另一方面去除了历史先锋派的精英局限,通过与黑人音乐、政治民谣、摇滚乐、波普艺术结合,文化激进技术扩展了它的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这方面正是历史先锋派的短板。这个方面最为巨大的成果就是俘获了二战后的婴儿潮。这个群体主要来自于战后新形成的中产阶级家庭,经济上的富足使得年轻一代有足够的时间与经历反思自己的身份政治问题:比如是否要像父代那样成为嵌入资本主义市场成功学模版中的一份子;比如如何看待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国家发动战争后带来的征兵问题,直接与每个人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比如对现有教育制度的不满(特别是对国家严密管控的巨大不适应);还有就是如何面对现实生活空间中不同社会文化族群之间的相互撕裂与区隔,以及每个人如何利用消费技术建构自身独特的文化身份问题。这些都是摆在这一代青年身上的新问题。通过多种形式的思想性写作与艺术实践,来自左翼的文化先锋很快对青年一代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使得文化行动成为具有巨大社会能量的运动,这就为“1968”的发生创造了社会条件。

电视成为了60年代双向度技术的典型代表。它既将国家意识形态宣传与公共事件输入到每个家庭的私人客厅,也通过电视中的越战画引发了对青年一代的刺激与震动。
第三,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反资本主义激进技术,它们所利用的媒介与信息技术,越来越表现出双向度特征。这个转变同样意义重大。虽然反资本主义激进文化技术很难在资本主义硬件体系中发挥作用,但已经开始在资本主义软件体系中发现了广阔天地。[[4]] 由于双向度技术可以被大众掌握,这给了过去沉默的大多数表达自己声音的可能。双向度技术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反资本主义服务,既可以服务于商品的包装,也可以成为批判商业文化的武器。五十年代的法国情境主义、英国新独立小组、美国黑山学院与垮掉的一代,六十年代的黑人平权运动、嬉皮士运动、以及多种多样的反文化运动,都是利用双向度技术与资本主义互动。这个时期的诸多组织都是利用地下刊物与地下电台扩展了自己对真实世界的影响,一旦现实空间的抵抗被媒介的力量放大一百倍之后,它就具有了动员更多样社会群体的力量,这样才能使得文化激进技术与真正与资本主义对抗。事实的发生也同样如此。在法国68运动早期,左派对媒体的使用很是成功,但到了晚期,右派对媒体的使用也重视起来,于是很快结束了“1968”。“1968”一定程度上就是一次媒体战争,早期是左派革命,后期是右派革命。“五月”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一次春季大扫除”。 极权资本主义与消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双向度技术取代单向度技术、新艺术语言的社会组织潜能三个角度的讨论,虽然仅仅是对“1968为什么发生”的有限维度的分析,但三者结合,已经初步将“1968”的结构模型做了粗略性的概述。这个模型其实在二十年代已经形成了它的结构性影子,并且,“结构”一旦形成,就会以结构的力量影响我们的今天,也会成为我们今天反观自身的透镜——这就是“后1968”的必然到来。


克里斯汀·罗斯(Kristin Ross)2002年的著作,《68五月及其后世生命》(May 68 and Its Afterlives)可被视为“对遗忘的诊断”。根据罗斯的考察,在七十年代中期,有另一种来自于媒体知识分子“五月之后”的说法开始冒泡。这种说法以五月遗产为名,开始了对广义的五月(包括五月之后的激进阶段)进行符合官方价值立场的改写。很快,“遗产”成为了遗忘,一种遗忘的史学,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写纸,最终在当代新自由主义语境中获得了所谓“共识”之名,完全模糊甚或抹去了68的绵延。也就是说,在法国有两种“五月之后”,一种是法国人简称的68后的左翼时期,一种是遗产/遗忘的后现代工业,而后者致力于埋葬前者。
“后1968”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关于“1968”的不断重构。关于“1968”事件发生的历史原因、过程与性质、在不同国家的变体等议题,都有着广泛的学术讨论。比如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Roszak)在《反文化的建构:对技术官僚社会及其青年反对的反思》(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 Technocratic Society and Its Youthful Opposition)一书中,对美国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分析涉及到越战、平权运动、嬉皮士、摇滚乐、性解放等诸多议题;而在法国,关于“1968”的讨论则总是与马尔库塞、德波、萨特、福柯、阿尔杜塞、巴丢等诸多观点差异的思想家群体有关,也会不断连接到对六十年代法国教育制度的批判以及戴高乐威权资本主义的科层化制度分析,还有关于从媒介角度作出的重要回顾和分析;在意大利,“1968”的议题则大多与“自主性”工人运动关系密切。基本上每隔十年,全球左派知识分子都会有一次关于“1968”主题的集中讨论。这些讨论既有共识性的认识,也有诸多观点差异的评论。我们看到,这些不同的版本之间差异极大,以至于越是被讨论,它的真实面貌就越是不可知。一方面,像黑泽明的“罗生门”一样,每个具体讨论基于特定的语境和立场需要,都有意无意地重构着“1968”的叙事,另一方面,关于“1968”的整体叙事随着当代资本主义进程不断发生变化,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性的需要。此外,“1968”模型最为让人震惊的地方是,这个模型会通过不断的变异与伪装,被不同主体生产出自己的拟像,每种拟像中都有真实的部分,也有虚假的部分,它们互相穿插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有时用理论掩盖了现实,有时理论叙事比现实还现实,它们是关于“模型的模型”。

詹姆逊,1984年特刊《六十年代,不辩解》(The 60s Without Apology)。这一专辑当然以美国的六十年代为中心,但也涵盖了全世界范围内同期的各类左翼运动。所涉及的题目有美国左翼传统、民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黑人武装斗争、法国68、理论变革、学生反叛、流行文艺、反殖民斗争、第三世界等等,也有亲历者的回忆文章和论争。

迈克·哈特(Michael Hardt, 1960-)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 1933-)奈格里是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的领导者和思想领袖。奈格里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后现代主义传统结合起来, 创立后现代革命理论 , 他是当今世界最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左派活动家之一。

安东尼奥·奈格里与迈克·哈特合著《帝国》(Empire,2000)、《诸众》(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2004)、《大同世界》(Commonwealth,2009)三部曲。他们尝试用“帝国”这个概念来描述去中心的、无疆界的、超民族国家的全球化政治秩序,用“诸众”这个概念来指认一种处在“帝国”秩序之下、而又反抗着“帝国”统治的历史主体。
“后1968”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它给我们今天带来了怎样的遗产。至少三种方向的激进技术遗产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新左派、右翼、技术乌托邦。新左派激进技术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多元文化主义的身份政治议题。这个议题继续在文化批判领域占领了话语权。首先体现在当代艺术领域的机制批判的兴起,身份政治议题广泛渗透到当代艺术的方方面面,全然超越了现代主义时期的美学语言本身,甚至通过有意识的反对视觉与美学霸权,从而将艺术引向背后更为广博的生产机制、展示机制、与收藏机制批判。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显然对此帮助很大。放弃了阶级分析立场与政治经济学视角后,新左派把工作重点放在了与激进文化政治直接有关的领域。对新左派而言,文化领域的抵抗与传统的工人阶级斗争已经发生很大区别,资本主义的斗争阵地已经不再是工厂,而是生活的所有方面。其次,性别政治、女权主义、环境主义都是68左翼遗产的产物。性别政治在今天早已成为显学,女权是68时期平权运动的延续,环境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修补代价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1968”是资本主义进入新自由主义以及全球化阶段后,所必然要面对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而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了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的文化注脚。 右翼激进技术是“后1968”第二个最主要的遗产,就是以金融为中心的弹性资本主义的转型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1968”时期资本主义遭受的批判,本身也是资本自身发展所需解决的问题。如1968时期对科层制以及大工业技术的批判,促进了资本主义从大规模标准化的福特制生产方式,向灵活积累的后福特制生产方式转型。这使得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资本、技术、商品、劳动力等要素跨越国界的流动与重组,将自身矛盾不断在地理空间转移,从而延缓了危机的爆发,变得更加有隐蔽性。此外,右翼的另一个遗产就是如何保证社会秩序的安全与可控性。反恐在2000后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治理技术被执行,50与60年代冷战期间的控制论技术被重新提起,并通过智慧城市这个极具掩饰性的概念,散布到当代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图1 60年代,许多热衷于嬉皮生活方式的人离开社会,重新形成具有前工业时代特征的社区。 图2 20世纪60年代初,计算机一直困扰着美国人的想象力。冷战技术工具形成的军工复合体,具体化以及强化了对僵化社会组织的机械遵从。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即互联网出现的前期,计算机开始代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协作的数字乌托邦,模仿的是嬉皮士们的社群生活理想,这些嬉皮士一开始就强烈反对冷战时期的社会技术格局。《从反文化到赛博文化》是第一本探讨这一非凡转变过程的书[[5]]。](https://pills-static.oss-cn-beijing.aliyuncs.com/uploaded/pills/research/content/2024/11/26/kla6vbvm0qb.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w_3000,limit_0/format,jpg/interlace,1/quality,Q_100)
图1 60年代,许多热衷于嬉皮生活方式的人离开社会,重新形成具有前工业时代特征的社区。 图2 20世纪60年代初,计算机一直困扰着美国人的想象力。冷战技术工具形成的军工复合体,具体化以及强化了对僵化社会组织的机械遵从。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即互联网出现的前期,计算机开始代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协作的数字乌托邦,模仿的是嬉皮士们的社群生活理想,这些嬉皮士一开始就强烈反对冷战时期的社会技术格局。《从反文化到赛博文化》是第一本探讨这一非凡转变过程的书[[5]]。

图1 Bonnie Ora Sherk, original drawing for Crossroads Community (The Farm),1974, San Francisco. 60/70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中出现的嬉皮士与社群生活回归,并不能被简单的理解为通过回归前工业生活方式从而与后工业生活方式产生距离,相反,这种社群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后工业“文化工人”工作生活一体化方式的预演。30年后,这种生活方式被吸收到硅谷科技精英的创业与生活方式之中,被作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模版,引导向进入自由的被剥削的现代数字与文化工人群体之中。 图2 Ant Farm collage drawing in Guerrilla Television, 93. 60/70年代嬉皮士的游牧生活的成立前提,本身来自于激进技术领域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可移动技术,越来越小的机器与设备,为塑造临时性的生活空间建立了可能。或者说,激进技术通过微小技术装置的发明与扩散,将自己的控制领域从城市、建筑、室内等传统空间,进一步扩散到未被征服的边缘地带与自然领域。这实际上是激进技术引发的微粒式城市化。

Absalon, Solutions, 1992, Video, color, sound | 7:30. 与60/70年代嬉皮士的时尚化的、表演式的游牧生活不同,艺术家阿布萨朗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发展出一种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修行生活与全球化时代消费社会批判相结合的激进形式。通过引用柯布西耶的建筑原型,通过一系列更极限的规则的设定,比如极小的尺度、身体作为边界、独自一人生活的反家庭/反社群生活实验,阿布萨朗将自我理解为一种激进技术的自我生活方式本身。即,不是像嬉皮士们打破既有规则,而是通过自我限定新规则,从而激进的抵抗社会的既有规则。

图1 格雷伯(David Graeber)关于直接行动网络的民族志(Direct Action)。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类学家格雷伯,是最近30年关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基因与行动方法的最重要的研究者与社会行动者。格雷伯详述了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直接民主”的组织原则。在另一本专著《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中他提出,相比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理论(纲领)和实践(组织)的有机结合。无政府主义者绝不是将纲领悬置在理论神龛,而是更加关注在具体的行动中智慧的发明“方法”。这种方法论路径,是对50/60年代德波与情境主义社会批判思想与本地化行动的真正继承。 图2 无政府主义的logo。
“后1968”第三个重要遗产是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技术乌托邦。它是对右翼激进技术与新左派激进文化技术的重要补充。其实无政府主义也是19世纪的遗产,它与马克思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是相伴相生的产物。大多时候,无政府主义与左翼都反资本主义。上文的正反两类激进技术的区分,就是把无政府主义激进技术与左翼激进技术作为一个整体对待的。但是,经过1968之后,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技术逐渐与左翼激进技术区别出来。典型例子就是参与到美国反文化运动的嬉皮士群体,在60年代晚期与探索计算机技术的专家在美国湾区形成了一个共同协作的团体,他们推动了对今天特别重要的个人计算机领域的极大发展。比如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在《睡鼠说了些什么:60年代的反文化如何塑造个人电脑》(What the Dormouse Said: How the 60s Counterculture Shaped the Personal Computer)一书中对这种隐秘联系的揭示。又比如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2006)在《从反文化到赛博文化:布兰德、全球网络与数字乌托邦的兴起》(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t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一书中对这段历史的回顾。[[6]] 在当代互联网领域,基于无政府主义的技术发明日益变多,比如病毒、骇客、维基百科、区块链、开源软件,等等。无政府主义倾向既批判资本主义的私人财产逻辑(所以表现出诸多共享性特征),但是,它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制度化方案(所以和左翼政治之间始终矛盾重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激进技术往往能超越传统伦理约束,在方法论,而不是在目的论层面,带来真正革命的“技术形式”与“社会组织形式”。比如社群自治,自我组织,民主协商,直接行动。在西方左翼思想家越来越停留在学院之中的思想批判,而与现实革命越来远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开启了现实行动的诸多发明。千禧年世纪之交所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无政府主义者直接行动策略的典型体现。综上所述,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在“激进技术发明”与“激进社会组织形式”两个维度,提供了批判与抵抗新自由主义精英政治的药方,所以在今天特别需要加以注意。

邱志杰2011年在《乌托邦地图》(局部)中对全球政治意识形态的图绘。邱志杰通过地形学的比喻,比如山脉、河流、铁路、群岛、海湾,用地理学特征物化了当代政治思想领域的谱系关系,从而为我们全局性的把握68之后的思想运动与理论话语,提供了一个反碎片化的地图。
从“新左派”、“右翼”、“无政府主义”三个维度对“后1968”与当代社会的联系进行梳理,是因为它们不但彼此区分,同时也彼此交织。比如,一旦从激进技术的角度审视现实秩序,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发生在重大的技术革命之后。”这个原因可以这样理解,重大技术革命引发经济增长与繁荣,但只能使得少数人更加收益,从而拉大社会贫富分化,导致社会极化。90年代以来的数字技术推动了这一轮全球化的巨大发展,使得精英阶层获利,但也带来无法克服的社会危机。过速的技术进化无法给社会流出调试的时间,从而出现大批的无用阶级,从而带来新新左派在2000年前后的反全球化运动及其批判。这是无政府主义同时与右翼、左翼的交织。另一个例子是,无论左派激进技术开始怎样具有革命性(特别是在艺术领域),后来都摆脱不了被市场收编的命运(这是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相互交织)。又比如,市场繁荣时期,会给左翼文化创造条件,而市场出现问题时,更容易导致左翼陷入低潮,更严重的是导致右翼民粹主义兴起以及国家垄断权力的上升,当下的美国、英国正是如此。在每种情境下,“激进技术”都是一般双刃剑,既开疆破土,也自损三千。

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包括《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1996)、《认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1997)、《千年终结》(End of Millennium,1998)。要真正理解后68时代激进技术对社会的激进形塑,卡斯特的三部曲是一把具有全球视野的关键性的钥匙。
“后1968”的当下紧急问题是,我们是否再一次来到了这个模型重新结晶的边缘地带?或者说,八十年代至今开启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其产生的社会代价是否又到了一个无法简单回避的时刻?诸多社会学家看到的事实是,全球资本流动、生产要素的全球再格式化、数字互联网时代不断深化的自动化技术,正在极速拉大固嵌在特定国家/地方、无法流动的社会边缘群体与全球精英群体之间的裂痕。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断裂》一书的序言中提到这样一个故事:他在90年代访问法国时从社会学家图海姆(Alain Touraine)那里得知,法国社会正在从一种金字塔结构演化为一种马拉松结构。在金字塔结构中,虽然每个人的地位不同,但还是整体焊接在一起的,至少彼此能互相看见。而对于马拉松结构来说,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群人掉队,这些人已经不是掉入底层,而是已经被甩出社会结构之外了。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著名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中,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即技术进化正在激进地使社会重新型构,进一步产生无用的阶级。这样的社会代价就是当前全球尺度各种激进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而这正是再一次“1968”模型到来的预演。 “后1968”正是通过主体性的稀释,通过将“文化革命”简化为一种“代际修辞”与“个性解放”,拥抱了新自由主义对更灵活劳动力的诉求,实现了既有资本主义积累结构的回归,甚至是向更高层面的发展。通过虚拟空间的无限激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无数个虚拟数字工厂中不停地劳作,从一个到另一个,直至两眼通红地耗尽最后一丝力气。从激进技术进化的速度的角度看,如果说十九世纪的工人阶级一生仅仅面临几次技术迭代,二十世纪中期的大众一生面临十次左右的技术迭代,那么今天的数字工人一生要面临上百次甚至更多的技术迭代——那些坐在电脑前面的码农甚至几天就要面临各种软件技术的更新,而人工智能正在利用效率逻辑系统来“设计”快递小哥的意外死亡。对建筑师、设计师这样的创意工人而言,命运也好不了哪里去。今天的创新性技术工人面临的是更为残酷的彼此竞争,这些工人的对手早已不是那个隐性的系统,而是每天要活生生地面对同样有着创新压力的同行。这早已不再是一种创作的快乐,而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绝望。“后1968”意味着右翼“激进技术”隐秘性的升级,也意味着左翼“激进技术”美学化的衰败。


激进设计,CASABELLA.N O. 367,1972。扩展来说,1972对建筑领域而言也许是1968之后最具有戏剧性的一年。这幅插图来自于CASABELLA出版人亚历山德罗·门迪尼(Alessandro Mendini)1972年在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购买的一张明信片,并在上面打上了“Radical Design”的字样。这个图像本身可被理解为激进技术与原始意义上的人的直接结合,用市场经济的图像和工具表达了一种诱人的激进批判。同年,MOMA举办了意大利“国内新景观”展,美国资本主义再一次通过景观化的展览消化了欧洲激进思想探索的成果,但去除了激进的政治基因;文丘里出版了《向拉斯维加斯学习》,预示了后现代社会符号景观即将在未来的社会中重新接管一切;库哈斯在纽约凭直觉绘制了“俘获地球的城市”,成为了写作《癫狂的纽约》的理论脚本;詹克斯用事件艺术的夸张宣布了现代建筑的死亡时间,也从社会空间维度真实揭示了20年后新自由主义时代更加剧烈的社会区隔的大规模来临;ARCHIZOOM结束了他们为期五年的理论项目“无止尽的城市”,避免了理论方案一旦落入现实设计所要遭遇的自我堕落;山崎实在纽约建成了只有46厘米宽的狭窄窗户的双子塔,再一次验证了心理安全、摩天大楼与经济危机之间的隐秘联系。这些相互矛盾的事件是“1968”的缩影,也是今天的寓言:我们此刻是否仍需要通过激进设计,严肃思考激进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危机?
历史地看,如果说资本主义以战争形式消化了第一次“1968”,以文化景观的市场吸收化解了第二次“1968”,那么现在,正在在以民族国家冲突的形式消化正在浮现的第三次“1968”,它们在性质上都属于经济发展脱嵌社会之后的系统弥合。这些弥合的目的是为了重新让资本主义经济有动力反弹,或者说,是为了迎接下一次“1968”模型的重启。实际上,无论是“前1968”、“1968”、还是“后1968”,它们都拥有相似的结构模型。这个模型既存在“解放”的一面,也存在“异化”的一面。既带来社会进步与解放,但也会成为异化社会的工具。从异化与解放的辩证关系看,作为内嵌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1968”模型,并非第一次具体的发生,也绝非最后一次。“1968”模型只不过代表着同时具有解放与异化能量的多种激进技术在特定时刻强烈对抗的一种特殊状态。它既不会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但也不会毫无作为,它会以否定性的阵痛疗法,刺激资本主义的持续进化。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虽然每次原因与机制都不相同,但在每次资本主义危机来临的前夕,都会出现一次程度上或大或小的“1968”。它既是对异化的批判,也是对解放的预演,如此往复循环。比如1871年巴黎公社后两年,是19世纪最为重要的1873-1893年危机,正是这次危机催动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度;1929-1941危机之前12年是1917十月革命,这次危机带来贯穿着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1968年之后6年,是1973-1980资本主义危机的到来,这次危机催生了资本主义从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型。资本主义世界危机与多种“1968”模型的反复显现,是一件事情。 本文的讨论思路,就是从两种激进技术相互缠绕的历史出发,在长周期进程中,检视激进技术、作为结构模型的“1968”、与资本主义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看它的前史、变体、以及与今天的关联。正是通过激进技术的角度,“1968”模型的复杂面向被具体的结晶;正是通过“1968”模型,激进技术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被清晰地检视;也正是通过激进技术与“1968”模型的双重透镜,当代社会转型所处的阶段能够被整体地定位。本文的讨论不是事件尺度的微观分析,或关于60年代的具体技术个案的研究,而只是一个粗略勾勒的地图。这个勾勒不是试图给出精确性的答案,而是试着将“1968”模型被不断重构后的碎片重新拼起。当前,一个被分解的“1968”,一个已经被消费的“1968”,一个正在显现在整个全球社会系统中的“1968”,正是我们此刻面临的社会事实:一边是从三十年全球化得利的全球超级阶层,另一边是技术自动化形成的正在浮现的“下沉阶层”,我们再一次要面临经济脱嵌社会所要面对的沉重代价,这正是我们展开未来具体行动的前提。(完) 注 [1] Raymond Williams,May DayManifesto 1968,(Anniversary edition of the classic political manifesto),Verso Books,2018 ,p10. 与当前通缩危机的争论密切相关的是,《1968年五一宣言》为战后共识失败后的社会主义英国制定了新的议程。它试图改变国家的性质,在金融和帝国之间打入一个木楔子,强调计划经济对所有人的重要性,并使英国脱离它长期致力于实现的帝国目标。今天,五一宣言的精神为更光明的未来提供了一个路线图。最初的出版物汇集了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激进声音。70个签名者中有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E.P.汤普森(E. P. Thompson)、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等。本段引文来自欧文·琼斯(Owen Jones)在书中的介绍,他给当代辩论带来了紧迫感和希望。 [2] 在诸多学者看来,1968不是一次阶级革命,不是一次生产方式革命,不是一次暴力革命,而是一次文化革命。1968就是经济发展速度超过社会整合速度时,以浪漫主义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激进社会的转型预演,直至形成了当代西方社会“政治正确”的基本准则。 [3] 对于法国而言,1968正是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20年的历史节点。在60年代的戴高乐时期,法国虽然在经济上一直高歌猛进,但已经无法像19世纪末那样通过扩张殖民地消化过剩资本积累,只能面对矛盾在自身社会内部爆发。对美国而言,1968正是越战突然失利导致资本消耗出现障碍,从而引发国内反战情绪积累到无法弥合阶段的产物。 [4] 在资本主义系统中,物质生产总是单向度的,它总是需要重型的资金投入、机器与厂房等基础设施,与此相反,非物质文化生产却可以是双向度的(不是必然是,比如好莱坞文化工业就仍是单向度的)。 [5] 弗雷德·特纳(fredturner)在这里追溯了旧金山湾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创业者群体的故事:布兰德(Stewart Brand)和全球概览(Whole Earth network)。从1968年到1998年,通过获国家图书奖的《全球概览》、计算机会议系统、之后的《连线》杂志,布兰德和他的同事促成了旧金山花卉电力公司(sanfrancisco flower power)和硅谷新兴技术中心之间的长期合作。由此,反文化主义者和技术专家们联合起来重新设想计算机作为个人解放的工具,建立虚拟的和决定性的另类社区,以及探索大胆的新的社会前沿。 [6]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冷战期间,基于军工背景的计算机体现的是僵化的组织与机械性的整合,然而,具有反文化倾向的嬉皮士们试图在湾区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基于平等合作的理想组织,一个协作的乌托邦。90年代互联网的发明是这种理想的产物,使得计算机重新成为一个个人解放的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各种超越现实约束的虚拟社区可以建构起来。 备注:感谢本文写作过程中来自王子耕的启示,以及郭博雅的仔细修正与建议。 作者简介 韩涛,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设计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 | 郭博雅 王子耕 编辑 | 丁亚楠